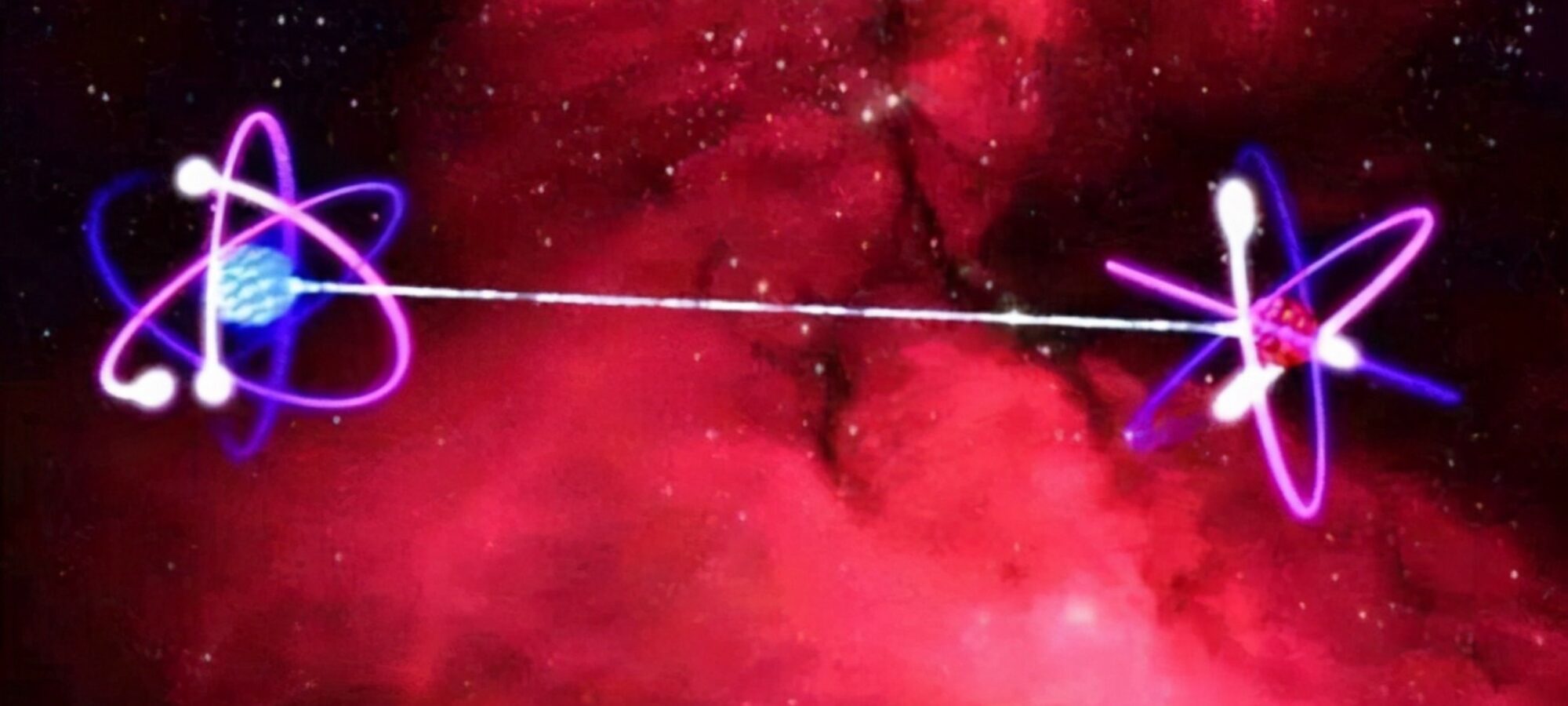一个又一个童话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穷困的老磨坊主,他有三个孩子,一头驴子,还有一只虎皮猫……”。这个以《穿靴子的猫 》而闻名的童话故事的开头来自其众多抄本之一。那么,在诸如上述猫一类的奇幻故事和当代物理学之间,难道存在某些共同元素吗?描述自然现象的数学公式冰冷而毫无生气,难道它们与充满美妙人情味的现实,比如那些讲给不同年龄儿童的故事、摇篮曲以及拥抱(我们将在下文中谈及)有什么共同点吗?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虽然科学必然会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向我们展示一个与日常生活经历极为不同的现实,但它不会将任何特定哲学观点强加给我们,而只是非常谦和地停留于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定量描述(以及在可能范围内的预测)。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些杰出的科学家虽然对物理量的数学描述完全赞同,但会在此后因为如何以更明确的哲学观点进行诠释而产生严重分歧[1]。此外,虽然数学表达不可或缺且无法放弃,但为了寻求其它更通俗易懂的方式,科学——特别是物理学——通常会在不考虑其丰富伦理道德教育意义的前提下,以与童话、寓言和隐喻等类似的形式作为解释科学概念的描述和叙事工具。
虽然明知物理学与我们即将使用的类比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仍然可以说,它所偏爱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俳句:这是禅师用以修行的一种诗歌体裁,由17个字音组成(遵照5-7-5规则),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强求对诗句进行任何确切的诠释。这种精炼的写作方式突显了基于语言以及我们死板的推理方式的局限[2]。为了说明某些物理量“不可确定”的特性,即无法确定某一事物所处的状态,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受东方智慧启示的文学体裁——公案 ,这是“一种表面看似荒诞的谜题,被许多禅师用以施教”[3]。中国及日本的神秘主义者对现实的矛盾性极为敏感,他们通常以看似怪异的形式对此加以揭示,以突显语言沟通中的不一致性,并展示现实最终似乎并不像某种“可嘉的常识感”所归纳的那样简单和死板。
当代物理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宇宙,但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一个确切的、可以理解的宇宙观,并同时摧毁了实证主义者的理性极端主义[4]和某些继承古典亚里士多德现实主义的绝对化立场,[5]。量子革命之后,世界不再是那个稳固而确定的现实,就像我们以往在理想中坚信自己所认识的那样[6]。智利作家本杰明∙拉巴图特(Benjamín Labatut)[7]指出,现实根本不会迎合我们的期望,而是具有千奇百怪、扑朔迷离和深不可测的特性:“科学不仅是方法,也是形而上学的狂热[8]。
虽然我们并不赞同将科学简单地视为对世界的另一种“神话式”描述,或是与现实两不相容(但也许更可信)的历史哲学性解读,但必须承认的是,科学界中存在着某种轻微程度的迷茫。虽然一方面,科学界某种可能的倾向是将理性视为一把火炬,但它的光明不足以照亮漆黑、迷宫般和不确定的宇宙;然而另一方面,它又感受着似火的热情,并在其推动下探索事物,否则这些事物将被简单地视为不可知的。
本文将尝试以一种简单方式介绍和解释物理学中的一个难题:它涉及一只猫——不是穿靴子的那一只而是著名的“薛定谔悖论”中的那一只——以及在量子力学中所观察到的一种促生玄妙的相互作用体系的趋势,即量子纠缠(entanglement)[9]。特别是对于薛定谔来说,他所提出的是一个被构想出来但并未经过实践的实验,即所谓“思想”或“概念”实验。在这种思想实验中,仪器被以简化的形式构想,以回避技术性困难,将注意力集中于问题的本质特征。以这种方式,实验结果经理论性“推算”得出:从它的基础到最终结果,都是通过应用有待测试的物理模式规则。在这些情况中,由概念性表述得出的推论时常会出人意料或自相矛盾。
一只半活半死的猫…
1935年,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0]或许因量子学描述世界的荒谬而感到恼火,以至于他可能是出于报复而想(设想)杀死一只猫。为了展示量子世界的不合理性,这位奥地利物理学家恶意地设计了一个残暴的悖论,使林奈[11](Linneo)所命名的felis silvestris catus(猫)在不到一个世纪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一个奸诈的互联网明星。
猫实验发生于关于量子力学诠释的激烈辩论中,其背景是哥本哈根诠释[12]与物理学界其他人士的对立,其中包括在20世纪初对新物理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薛定谔。让我们在此简要回顾一下哥本哈根诠释:最早出现且最为物理学专科所接受的诠释起源于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3]和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4]于1927年左右进行的工作。他们扩展了马克斯∙博恩(Max Born)提出的波函数概率诠释[15]:根据这一量子系统状态的数学表述体系,对于量子实体的物理特性,在对其进行测量之前,有关数值及存在的问题毫无意义。对于这种系统在被观察之前的完全不可知性,无论是在认识方面还是对于“事物”存在本身的不可知,薛定谔均感到不满。
他于是提议:“将一只猫及下述可怕仪器一同关入一个铁盒子中,但必须保证仪器不能被猫直接抓住”[16]。这个可怕的仪器是一个含有少量放射性物质的盖革计数器(contatore Geiger)[17]。从概率上讲,这个极小的含量可能在一小时内使放射性物质的一个原子衰变,但同样可能的是不发生任何原子衰变。倘若原子真的分解并衰变,计数器就会发出信号并启动一个锤子,锤子会打破一个氰化物瓶子并使猫中毒而死。否则,一切都将继续保持原状。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猫在一小时后的生死并没有任何确定性:如果没有原子衰变,猫会若无其事地继续它平静(或不安)的活动;如果发生原子衰变,猫则会被毒死[18]。“用以描述整个系统的波函数竟然推理出其中的猫既不是活猫也不是死猫,而是处于生死各半的混合状态中”[19]。这个活猫-死猫系统始终处于不确定和“不可决断”中,直到盒子被打开、猫被观察到为止。
这个悖论中的困境涉及一个事实,那就是,直到被观测到之前,就像同时处于死-活叠加态中的猫一样,某一宏观系统也有可能同时处于不同状态的叠加态中。这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此外,量子力学描述的物质“状态”也很难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宏观经验相契合。量子物理学不可能以被称为“经典”的方式来描述物体[20],而是必须借助于对世界的“概率”表述:它是我们的现实之根基。例如,为了表述一个粒子所在的位置,它必须被描述为仿佛可以同时处于所有可能的空间位置。空间中的每一个点都对应着一个概率,对粒子的观察结果将显示它“确实”处于那个位置。但是,观察行为会对系统带来不可逆转的修改,因为一旦在一个位置上被观察到,粒子就会永久性地占据那个位置(即它在那里的几率为1),并因此而不再处于“叠加状态”。
让我们回到那只猫。它的症结在于,薛定谔所指的是“整个系统的波函数”,而不是单独的猫的波函数。事实上,该理论指出,“原子+猫系统”是经量子相关性状态描述。因此,处于生死叠加状态的不只是猫本身,而是整个系统。由此而出现的是一个深刻的困境:一方面,原子的行为由量子力学定律描述;另一方面,这些定律似乎也能对一个(巨大的)生命体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样它就会发现自己与量子世界的“拥抱”:但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日常看到的不是活猫就是死猫,而绝不是处于半生半死混合状态中的猫。然而,量子物理学似乎告诉我们,即使是(大型)生物也能以生死各半的状态存在。于是,宏观世界似乎产生与微观世界的量子纠缠 [21]。那么,我们的宏观世界是否也必须受制于量子力学的变化无常呢?这就是所谓的“测量问题”。
哥本哈根诠释指出,如果一个量子系统,比如盒子里的放射性原子,同时存在于未衰变和衰变的叠加状态中[22],任何测量都将“迫使”该系统明确呈现叠加状态中的一种,而且只有一种:或是未衰变或是衰变。从那一刻起,叠加随即消失,也就是所谓的“波函数坍缩”。哥本哈根诠释并未对“坍缩”的确切模式加以追究,它甚至很可能根本无意解决这一问题:有些事物是可以解释的,另一些事物则不可诠释;物理学家(真正的物理学家)很清楚科学知识中所固有的局限性,他们同时深刻体会到这种某些现实的不可诠释性[23]。
量子化拥抱
因此,上文中所谈的猫实际上被一个复杂局面比它可能更喜欢玩的毛线球要复杂得多。1935年同年,令人疲惫的关于哥本哈根诠释的争论促生了另一个思想实验,即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EPR)实验[24],其焦点正指量子纠缠现象。在《物理现实的量子力学描述能否认为是完备的?》[25]一文中,三位作者提出,遵照定域性原理(Principio di località)这一被视为科学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量子力学必然是不完备的:尽管它取得了一些显著的结果,但仍是“蹩脚的”。概括地说,根据定域性原理,在彼此相隔的物体之间,其互相影响不能瞬时产生,而是需要至少相当于光穿越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所需的时间。因此,对于EPR来说,波函数有所欠缺,尤其是在“哥本哈根学派”作出的相关诠释中存在着不足之处:亚原子世界现实所包涵的元素多于量子力学所描述的元素,必须超越并完善物理模型,将其与其他因素整合,即加入“隐形”的“变量”。
让我们总结一下大卫∙博姆(David Bohm)对实验的描述[26],并补充一些从后续发展中获得的元素。爱丽丝和鲍勃是两个相隔光年之遥的研究人员。这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距离,而并非比喻:他们分别身处位于两个遥远的星系,无法进行即时通讯。爱丽丝试图发送给鲍勃的每条信息,虽然以光速传播,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一个自旋为0的粒子位于两位科学家之间,它衰变为两个电子并向相反的方向移动,直到到达爱丽丝(电子A),和鲍勃(电子B)[27]。由于初始粒子的自旋为0,两个新粒子的自旋之和必须为零。因此,如果电子A的自旋为+1/2,那么B的自旋必定为-1/2,反之亦然,它们顺着可能的量子取向“轴”自旋。鲍勃并不知道爱丽丝会选择哪个轴来观察她的电子自旋。只是,一旦爱丽丝测量A的自旋,不用通过对B的测量便可立刻获知其自旋数。同样,如果鲍勃进行测量,即可确定爱丽丝的相应数值。
但这怎么可能呢?电子A如何与B进行关于自旋数的即时交流?而且最重要的是,如何得知爱丽丝选择哪一个轴进行测量?对爱因斯坦来说,这显然(而且是不允许的)违背相对论:它促使我们承认,从A发出的信号以超过光速的速度传播,在瞬时内到达B;因此,在粒子A和B被测量之前,其中必然存在包涵自旋量子数和其他信息的“某些隐形物”。然而,根据哥本哈根诠释,在进行测量之前,两个粒子均不具备任何确定的、方向明确的自旋状态,而只是作为可能的叠加状态存在。
正如物理学中并不罕见的情况,为推翻一个概念而提出的概念最终却成为它的验证。EPR悖论亦然如此:本为揭示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而提出的理论,结果是确认了量子力学与宏观世界经验从根本上的相悖。随后的理论和实验发展[28]巩固了量子物理学的地位。物理学家约翰∙斯图尔特∙贝尔[29]以其“贝尔定理”提出了一系列不等式,即所谓“贝尔不等式”:如果粒子A和B的自旋测量以经典形式分布,即根据我们有直观和习惯经验的宏观物理学,这些不等式就会出现。通过反复的实验,贝尔的不等式始终被违反。因此必须承认,量子纠缠确实存在[30]。同样,根据贝尔不等式,任何带有隐变量的区域物理理论都无法重现量子力学的预言。虽然一点也不直观,但似乎应该摒弃定域性:世界的基础远比它向我们所呈现的要错综复杂……
美妙的物理学
因此,在进行测量之前,量子物理系统的实际属性似乎根本“不存在”,而作为描述物理世界基础最可靠的最小核心,波函数是计算实验结果概率的数学工具,也是科学应该讨论和关注的唯一因素。量子力学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扇令人困惑的大门,它不顾我们的认知痛苦,把大自然已安排得井然有序的事物像谜一般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扇大门嵌立在以下两个难以置否的轴心上:1)态叠加原理:这一原理迫使我们承认,一个系统既可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又可处于两者的任何一种组合状态。在状态A和状态B之间可产生第三种可能性,即A和B的组合,但它是不可知的。当对系统进行观察时,它就“坍塌”为一个确定的状态,而之前的不确定性就会消失,遁入一层无法窥视的面纱。2)非定域性:一切似乎都是如此神秘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事实上不可能追溯到现象的“一个”明确个体性。一个状态A的存在是因为“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星系”[31],一个状态B不但已经发生,而且也许已曾被观察到。
经典物理学观点及世界观若是扎根于日常经验或是过于死板的现实主义,就可能在那些“遮掩”和“揭示”现实的假象面前心生恐惧。我们对自身存在的感知好比一个小岛,虽看似平静,却充满未知系数,在混乱的无限之洋中不安,永远无法冲破“无限性”这一难关。这让人不由想起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32]。它们指出,在任何逻辑系统中,总会有一些真理,虽然是真命题,但在该系统中无法被证明,而且,通过应用相同的规则,人们可以同时证明一个命题既是真的也是假的。连同这个不甚令人安心的图像,量子力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概率和不确定性的景观,其中混沌状态(caos)似乎是基本主旋律。难道我们必须承认“为自己的知识所付出的代价是丧失我们的理解力”[33]?这是自相矛盾的。
然而,混沌并非纯粹的无序,科学家们对此有所了解并有所感知。他们非但丝毫不会为此而气馁,反而将困惑视为一种挑战,让他们继续朝着未知的召唤迈进,认识到事物深处的某些东西顽固地逃避我们的理解,而需要解开的主要结症正是我们自身的想象力危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动力,赋予新的宏大叙事以生命,并同时借助于一种微妙的“新物理学”,从陈旧僵化的历史废墟中描绘出一幅新的世界宏图以及包罗万象的科学,以求与现实相联。一个现实只有在乍见时才会令人恐惧;只会让那些畏惧一切存在事物之复杂性的人感到不安,而这些事物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网络,能够揭示新的和不可预测的现象。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美妙方式…
有件事令人欣喜: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意大利人乔治∙帕里西[34]不仅在数学公式的复杂性中大展身手,而且能够乐观地潜心于自己编写的童话故事中。他的“儿童”故事的结尾会是以下这样的句子:“他们整天沉浸于吃喝玩乐中”,或是:“他们送给了女孩一束美丽的水仙花”,亦或:“从那天起,国王再也不说‘我想要’了,他总是亲切地对待每一个人”[35]。这种勇敢的物理学像童话一般,满怀憧憬……
- 参阅P. Beltrame, «Forse Dio gioca a dadi?», in Civ. Catt. 2021 I 450-461. ↑
- 参阅F. Capra, Il Tao della fisica, Milano, Adelphi, 1982, 51. ↑
- 同上。 ↑
- 抛开对任何一种思想形式所必须的具体及细节性关注,我们可以将实证主义概括为19世纪上半叶诞生于法国的一场哲学和文化运动:它虽然并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组织系统,却认识到在不同程度上宣称自己属于这一派系的代表者对科技进步的信任,从而使实证主义被奉为有用知识的唯一源泉。 ↑
- 自诩现实主义者的哲学家认为,真理实质上是概念与独立存在的现实相对应的一种形式。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对于“现实主义”的立场,现实独立于我们的概念框架、语言实践、信仰和经验而存在。在中世纪哲学中,圣多玛斯∙阿奎那是主张这一理论的中坚人物。他追随亚里士多德,将事物的本质置于事物本身中:在某种意义上,事物本身是那些通过我们的头脑加工的概念之源泉。 ↑
- 参阅C. Rovelli, Helgoland, Milano, Adelphi, 2020; 一个更小说化的叙述可参阅B. Labatut, Quando abbiamo smesso di capire il mondo, ivi, 2021. ↑
- 本杰明∙拉巴图特是一位智利作家,1980年出生于鹿特丹,14岁时移居智利圣地亚哥,至今仍在那里生活。 ↑
- B. Labatut, La pietra della follia, Milano, Adelphi, 2021, 47. ↑
- 纠缠在意大利文中可被译为量子“相干性”(correlazione)或者更具魅力的“量子困境”(intrigo)。 ↑
- 薛定谔(Erwin Rudolf Josef Alexander Schrödinger,1887年8月12日,维也纳——1961年1月4日, 维也纳)是20世纪对量子力学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物理学家之一,以他的名字而命名的方程使其赢得了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 林奈(Carl Nilsson Linnaeus,1707年5月23日, 罗斯胡尔特[Råshult]——1778年1月10日, 乌普萨拉[Uppsala])是瑞典医生、植物学家、自然学家和学者,被视为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 ↑
- 为了全面了解哥本哈根解释,可参阅:G. C. Ghirardi, Un’occhiata alle carte di Dio, Milano, il Saggiatore, 1997(特别是第4-7章);C. Rovelli, Helgoland, cit.;P. Beltrame, «Forse Dio gioca a dadi?», cit. ↑
- 尼尔斯∙亨利克∙大卫∙玻尔(1885年10月7日,哥本哈根——1962年11月18日,哥本哈根)是一位丹麦物理学家,也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
- 沃纳∙卡尔∙海森堡(1901年12月5日,维尔茨堡——1976年2月1日,慕尼黑)是一位德国物理学家。1932年,他因“创造量子力学 ”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
- 马克斯∙博恩(1882年12月11日,弗罗茨瓦夫[Breslavia] ——1970年1月5日,哥廷根[Gottinga])是一位加入英国籍的德国物理学家,他因量子力学,特别是因其对波函数的概率解释而获得1954年诺贝尔物理奖。 ↑
- E. Schrödinger, «Die gegenwärtige Situation in der Quantenmechanik» («La situazione attuale della meccanica quantistica»), in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23 (1935) 812. ↑
- 盖革计数器是一种测量辐射的仪器,特别是那些来自原子及核衰变的辐射。 ↑
- 有趣地是,此实验的设定前提是:猫不能有九条命;此外,在被囚禁于这个诡诈的系统中时,它也不能发出能够被人听见的叫声。 ↑
- E. Schrödinger, «Die gegenwärtige Situation in der Quantenmechanik», cit., 812. ↑
- 我们所说的“经典物理学”指的是能够很好地描述日常宏观现象的物理学,特别是始于伽利略并由牛顿正式确立的力学。 ↑
- 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个主题。 ↑
- 在这一点上,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可能会更为公正和宽宏。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认为,实体除了现实(attuale)存在外,还具有潜在的(potenziale)存在,它具有不明确的真实特征(如今通称不可观测性)。准确地说,它们已经潜在于根据其自身模式存在的事物中,只是尚未显露而已。 ↑
- 参阅J. S. Bell, Dicibile e indicibile in meccanica quantistica, Milano, Adelphi, 2010; P. Beltrame, «Forse Dio gioca a dadi?», cit. ↑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年3月14日,乌尔姆——1955年4月18日,普林斯顿),可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家,他是一位加入瑞士和美国籍的德国物理学家。1921年,他因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特别是因“光电效应定律” 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鲍里斯∙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 塔甘罗格,1896年6月26日——辛辛那提,1966年11月28日)是一位归化美国的俄罗斯物理学家。内森∙罗森(Nathan Rosen 1909年3月22日,布鲁克林-1995年12月18日,海法)是一位归化以色列的美国物理学家。 ↑
- A. Einstein – B. Podolsky – N. Rosen, «Can Quantum-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 Complete?», in Physical Review 47 (1935) 777-780. ↑
- 大卫∙约瑟夫∙博姆(Wilkes-Barre,1917年12月20日——Hendon,1992年10月27日)是一位美国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博姆力学”的发起人,这一学派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经典”量子力学的观点。以其不同于常规的观念,博姆也对神经心理学和心灵哲学做出了贡献。 ↑
- 尽管并不完全符实,但人们可以把基本粒子视为微小的陀螺,而自旋是这些量子旋转所围绕的轴。在物理学中,包括电子在内的基本粒子属于简单粒子,不由其他子元素组成,其自旋只能为分数(±1/2)。 ↑
- 比如贝尔定理和阿斯派克特的量子相关实验。阿兰∙阿斯派克特(Alain Aspect,阿根,1947年6月15日)是一位法国物理学家,曾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国最大的公共研究组织)研究主任,理工学院教授及法国科学院院士。他因其在量子光学和原子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获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金奖及沃尔夫奖。 ↑
- John Stewart Bell(贝尔法斯特,1928年6月28日——贝尔法斯特,1990年10月1日)是一位北爱尔兰物理学家,他提出的贝尔定理被视为当代量子力学中最重要的定理之一。 ↑
- 关于量子纠缠和贝尔不等式的出色讨论,可参见G. C. Ghirardi, Un’occhiata alle carte di Dio第8-10章,或者:J.S.Bell的《论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悖论》中找到,见同上,《量子力学中的可说与不可说》,前引,20-30。 ↑
- 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所创《星球大战》萨迦的著名片头。 ↑
- 库尔特∙弗里德里希∙哥德尔(Kurt Friedrich Gödel,1906年4月28日,布吕恩-1978年1月14日,普林斯顿)是一位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对20世纪的科学及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
- B. Labatut, La pietra della follia, cit., 48. ↑
- Giorgio Parisi,1948年8月4日出生于罗马,是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他在量子场理论、统计力学和复杂系统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因对复杂系统的研究而获得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目前在罗马大学(La Sapienza)大学物理系任教。 ↑
- 参阅https://chimera.roma1.infn.it/GIORGIO/favol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