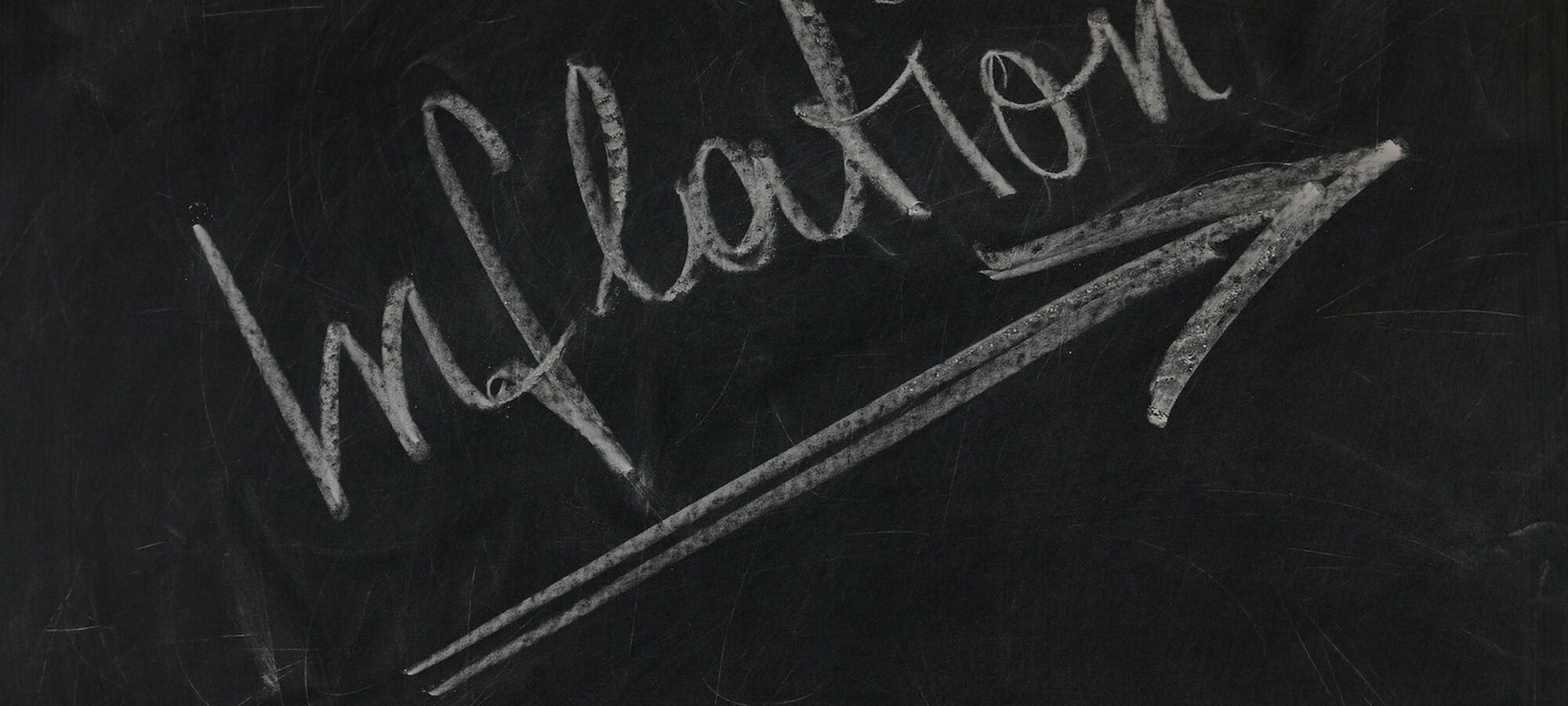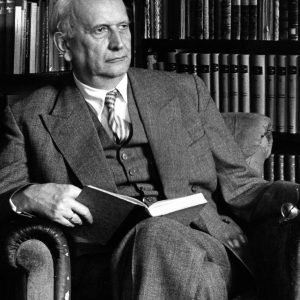经济学家没有以任何方式预测到全球性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目前的年通胀率已达8%,且可能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中持续。某种程度上,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四十年前就将抗击通胀定为绝对优先于其他政策的选项,许多西方中央银行如今皆认为必须效仿美国联邦储备的反通货膨胀政策[1]。然而,美联储刚刚决定提高基准利率,这是在数十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这一决定决不是对通货膨胀的“技术性回应”。实际上,它会加大使全世界面临一场新的金融崩溃风险,与2007-2009年的情况相似,甚至更严重,而且,可能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伴随类似希腊出现的公共债务危机。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是否存在其他的公共政策选择?
通货膨胀?一切皆归根于能源及原材料问题
西方国家目前正遭受着4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通货膨胀[2]。由于不同行业及各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涨幅不一,一些家庭—通常是最弱势的家庭—实际上面临着10%的年均通胀率。西方工资很可能无法跟上这一趋势,从而导致家庭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其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持续下滑了四十年[3],由此,尽管生产力越来越高,家庭却变得越来越不富裕。现今,绝大部分的家庭将被急剧“变穷”。
正如拜登总统2022年6月10日的讲话指出,一些政治领导人将这通货膨胀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然而,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化石燃料供应中断在目前的通货膨胀中占有一定比重,但远不足以成为它背后的驱动力。事实证明,通货膨胀在2022年2月24日开战时便已接近目前的水平。一些经济学家将此归咎于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冬季医保危机期间为最贫困家庭拨出了1万亿美元的公共开支。疫情封控解除后许多供应链尚在恢复期间,这些贫困家庭在消费这笔款项的同时点燃了通胀的导火索。即便是这种解释也同样无法令人信服,因为欧洲并没有像美国联邦政府一样,以相应的力度支出应急款项,却同样遭受到类似的通胀打击。此外,以能源为例,其价格在2020年中期便已开始上涨,包括封控解除前以及美国低收入家庭消费储蓄盈余的假设之前。
实际上,通货膨胀的最初原因是:在新冠危机后的经济重启中,化石燃料生产相对定量配给的情况抬高了能源价格。据世界银行估计,能源价格在2019年底至2022年2月期间上涨了56%[4]。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一增长并不是由于商品衍生品市场中交易者的投机行为:事实上,当时许多投机者在恐慌中从次贷资产中撤出了资金,并将其投资于石油衍生品。今天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在那段时间,能源价格在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期间甚至暴跌了60%:全球至少有一半经济活动被迫暂停,这造成能源需求的下降,并从而导致了能源价格的下跌。同样,碳氢化合物出口国的能源生产基地在疫情封锁期间被关闭,对勘探新油气田的投资也显著下降。为什么能源价格会从2020年中期开始飙升?原因是黑金和天然气生产面临一个瓶颈。
全球常规石油采量已于2006年达到峰值[5]。从那时起,如果不采用非常规技术(水力压裂岩石、页岩等),黑金年开采量的增加从技术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了解通过所有技术(常规和非常规)进行的全球开采何时将达到峰值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是,越来越多的石油工程师对这种情况在本十年内即可能发生的看法表示认同,所有人都一致认同的年限是2060年。这一重要地质现象业已临近的征兆之一是近年来石油EROI(“能源投资回报率”)的暴跌[6],因为开采我们所需要的石油需耗费越来越多的能源。这些地质因素的制约早已为人所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化石燃料价格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低的原因,可是,世界经济尚未步入向可再生能源转化的轨道(全球80%的能源消耗仍然来自化石燃料)。我们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尽管这种价格的增长完全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可以解释总体通胀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和对能源需求的增加,连同因地质条件制约而愈加艰巨的供不应求。世界原油价格在2020年6月至2022年2月期间翻了一番,达到自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世界煤炭价格在2020年6月至2021年9月期间涨至三倍以上,然后维持在2008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又开始下降,直至2022年1月达到7%的降幅。上述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煤炭和石油在发电方面的部分可替代性,因为在另一方面,煤炭开采远未接近其峰值。
– 此外,还有技术性或气候性灾害:2021年3月的苏伊士运河堵塞;2021年夏天西伯利亚一家天然气加工厂的火灾;2021年夏末墨西哥湾产油区的艾达飓风;中国在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下继续施行疫情封锁,使全球价值链中一些关键厂家的运作持续减缓;由干旱造成的台湾缺水使半导体生产(70%产自台湾)减缓。
– 再有,2021年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紧张局势。莫斯科(向欧盟提供40%的天然气消费)在要求北溪2号管道投入使用的同时拒绝在2021年10月之前增加对欧洲大陆的出口。此外,北溪1号管道因维修而被关闭已有数月之久。
– 漫长的冬季和俄罗斯供应量的下降使欧洲天然气库存降至异常低点。2020年5月至2021年11月期间,世界天然气价格增长至五倍,维持于2008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并随后在2022年2月之前下降了13%。
– 自2022年2月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紧张局势空前升级。我们也在考虑经济制裁,尽管这些制裁还没有完全实施,例如德国仍不愿放弃俄罗斯的天然气,但它们已在助长化石碳氢化合物价格的飙升。欧洲天然气价格在2020年5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增长了12倍。因此,它超过了2008年9月次贷危机期间创下的66%的峰值。然而,在2020年4月至2021年10月期间,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仅”上涨了2.6倍,远远低于化石碳氢化合物价格在次贷危机期间所创的水平。因此,欧洲由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而遭受的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打击远远高于美国。尽管有其他靠近欧洲的供应来源––例如阿尔及利亚––,这也该为有效实施去碳化提供进一步的助力。
中央银行的反应
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对能源和原材料在通货膨胀中的核心作用存在误解,因为几乎所有他们使用的模式都不包括它们:它们被认为是经济生活中的次要因素,但所有企业家都知道,长时间的停电会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后果[7]。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所持信条一致,中央银行管理部门坚信,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就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他们认为,通货膨胀只能是由于流动货币过剩的原因。因此,为了控制通胀,应采用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应对两次石油冲击引起的通胀而对美国经济施加的同一处理方式,即大幅提高美联储(Fed)的基准利率[8]。
2022年6月15日,美联储因此宣布将短期基准利率提高到1.75%。这一0.75百分点的增长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增幅。此外,美联储宣布计划在2023年内将这一利率提高一倍。第二天,英国和瑞士央行也大幅度提高了其基准利率。欧洲中央银行(ECB)则决定不于6月份采取行动,而只是在7月份将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
通过这种方式,美联储希望重演1980年的“沃尔克冲击”,或者至少希望对使用这一利器的展望会刺激华尔街对原材料价格下跌的投机。由于原材料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比现货市场的比重大得多,预期目标是投注于价格下跌的投机活动足以推动价格下跌,从而避免美联储真的将这种威胁付诸于行动。在20世纪80年代,美联储高管所强加的暴力加息政策被冠以成功之名:通胀被有效地驯服了,但其代价是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原因很简单:商业银行经常需要在跨银行市场上进行再融资,因此以接近中央银行所设定的短期利率进行借款。短期利率的上升自动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再融资成本,商业银行立即将这一成本转嫁于它们向客户收取的利率和贷款条件。价格上涨和信贷条件收紧迅速“扼杀”了投资和消费。经济进入了衰退期,失业率上升,价格下跌。然后,生产系统将因这种缺乏投资而遭受多年的萧条,而许多经济行为者,包括家庭和企业,将在此期间破产,更不用说伴随着这种现场实验的社会磨难。时至今日,许多经济学家似乎仍未从这一灾难性事件中吸取教训,面对通胀的症状,他们难以区分能源和某些原材料(包括农业原材料)配给的原因,所以采用同样的补救措施。最终,高烧也许会消退,但与此同时病人有丧生的危险。
更重要的是,当今的情况比1980年代要复杂得多。事实上,自1985年起,每桶石油的价格便已明智地恢复到1973年的水平,因为没有任何地球物理因素的限制可阻止欧佩克卡特尔增加其年产量。当时的地缘政治有利于那些先后于1973年和1979年无情停产的人恢复生产,使石油价格重新下降,从而将通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于低水平,超过了“沃尔克冲击”的效应。
正如当时一些经济学家未能意识到通胀来自于石油冲击,同样地,他们也无法明白与其货币冲击疗法中期“成果”相关的主要因素并非利率上升。如果是这样的话,随着利率的下降,价格应该开始回升,因为在此期间,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并未减少。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而证实了通胀的深层根源并非货币问题。另一方面,如今也根本无法保证实现类似于1985年的“正常化”。如果这必须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因为乌克兰冲突不允许恢复和平的地缘政治,还是因为非常规石油开采已进入高峰期,或是由于其他不可预见的复杂情况的阻碍,例如,尽管华盛顿的迫切需求,沙特阿拉伯无法持续增加其黑金的产量——那么,随着2022-23年的经济衰退,价格暂时下跌,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即滞胀,其中价格将继续被化石燃料抬高,而西方(以及全球)经济则将由于其中央银行的反通胀“疗法”而停滞不前。在欧元区,滞胀的幽灵更具威胁性,因为近期的欧元下跌(其价值于2022年夏季跌破美元,为20年以来首次)意味着进口价格的上涨将助长通胀。
此外,第二个恶化因素比前者更具威胁力,即我们在过去的40年中建立起的资本流通和金融市场国际架构,它在20世纪80年代仍处于萌芽阶段[9]。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在沃尔克和里根时代并不存在的双重投机泡沫之巅,它们是金融泡沫和西方主要国家首府的房地产泡沫。
新一轮金融崩溃的威胁
如今的金融资产高估已不是什么秘密。自2008年以来,股票指数已经上涨了320%,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增长甚至不足30%,其实际比例为1比10。因此,可以解释资产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经济价值的创造,而是投机。怎么可能呢?这是由于2008年后各中央银行所实行的超低利率政策。
当然,有些人认为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合理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政策,被大大削弱的全球银行系统可能无法在2008年危机后幸存。这种解释只有一半的说服力:事实上,如果中央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只是起到了吗啡的作用,让金融“病人”不至于被他的伤口压垮,那么通过这种治疗而争取到的时间,从逻辑上讲应该是用来整顿国际金融体系的。然而,尽管许多承诺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报告、会议、国际峰会等等,在确保西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安全方面的成果却寥寥无几。
在欧元区,为确保银行系统安全而于2009年成立的欧洲银行联盟已被证明基本上是无济于事的。在2015年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中,本人曾指出,如果像2008年那样的危机再次发生,在没有大规模国家援助的情况下,欧元区的大多数银行将会倒闭[10]。在美国方面,巨型银行已经为资本重组做出了具体的努力,它们已不像2007年或欧洲同行那么脆弱。这可能是美联储显得比欧洲央行更“勇敢”的原因之一。它并不(太)害怕其主要银行会倒闭,而欧洲央行则非常清楚,利率的突然上升对欧洲银行系统来说可能会是致命的,该系统自2008年以来,有赖于法兰克福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幸存。矛盾的是,直到现在,欧洲银行系统给人的印象是“幸存”得很好,并在重新获取巨大利润(银行股票的回报率为每年10-15%,而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对慢了五倍),从而带来了2007-2009年的一页仿佛已成旧事的错觉。实际上,银行利润的亢奋只是因为欧洲央行的慷慨大方:人工输氧的巨大流量使私人银行飘飘然,突然“忘记”清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复督促规范化的秩序[11],而且明知生态转型将终结其依赖化石燃料的商业模式[12],它们持续处于严重的资本不足和绿色洗涤(green washing)。
2014年,能源价格急剧下降,再加上工资压制(自1990年代以来减缓了实际工资的调整)和银行信贷以牺牲实体经济为代价向金融市场的调整,导致了通货紧缩,即负通胀(在2014年底非常轻微)。2014年8月,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甚至发起了一个通货紧缩警报。由于担心欧洲陷入通货紧缩,法兰克福的中央银行因此开始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务,并在较小程度上通过创造货币而不进行“消毒”(资产购买计划 [Asset Purchase Program ,APP])购买私人公司债券。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从2014年底到2018年,欧洲央行作为其资产购买计划的一部分,注入了愈3.8万亿欧元,而2020年推出的大流行紧急购买计划(Pepp)涉及每月高达1400亿欧元的购买,在2022年总计超过1.7万亿欧元[13]。
然而,这种凭空(ex nihilo)创造的货币是间接的,因为其受益者是机构投资者(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最终,这些投资者实质上将这种免费甘露投入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在一个低利率的世界里,金融投机比年增长率低于3%的任何实体经济投资都更有利可图。相比之下,一个高杠杆金融赌博每年的收益率可达30%。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欧洲央行允许各国以较低的成本借款,但因此反而助长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投机泡沫,也降低了公民储蓄中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欧元资金之回报,例如人寿保险投资。唯一真正从这一史无前例的政策中受益的只有金融投机者。
在大洋彼岸,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了非常类似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中央银行当今所面临的困境是:如果继续实行其低利率货币洪水政策,它们将继续助长金融资产的通胀,且将遭到助长国内通胀的指责(无论是对是错)。此外,通胀使实际利率为负值,即使从长期来看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债券界现在是在亏本,而不是让富裕的储蓄者从中获利。因此,面对债券持有人的抗议,维持过低的名义利率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通过提高利率,中央银行会将金融领域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实际上,那些目前参与在近十年中价值爆涨的金融活动的投资者,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有通过负债才得以购买这些金融资产。事实上,私人债务如今已达到历史空前水平,相当于世界GDP的160%,远远超过了公共债务。投机者必须偿还他们的债务,或者至少偿还债务的利息。在一个增长仍然非常疲软,而且中国现在已拒绝将其贸易盈余再投资于西方金融领域的实体经济中[14],这些负债的投机者除金融领域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偿还他们的债务。因此,他们绝对需要继续实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便能够借到必要的流动资金来偿还债务。换言之,股票及其衍生品的世界需要将货币政策变成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15],才能避免崩盘。相反,债券和名义固定收入的世界则需要立即减少通胀并提高利率,以避免萧条。很难在今天预见这两个行为体中的哪一个会最终将自身利益强加给中央银行。特别是由于正在登场的第三个行为者,即过度负债的国家本身。
走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1980年代沃尔克政策的虚幻“成功”与现阶段的第三个重要区别,就此而言,与公共债务相关。四十年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已陷入主权破产危机之中,而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才刚刚开始上升。今天,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公共债务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并不存在所谓的“神圣”门槛,致使一个公共债务超过这个门槛的国家必然破产。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试图证明90%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不可跨越的卢比孔河(Rubicone),但一个学生后来证明他的计算是错误的[16]。与此同时,日本的公共债务超过其GDP的250%已有十多年了,但仍未发生违约。至于希腊,其债务与GDP的比率目前约为200%,高于2010年“希腊公共债务危机”开始时的水平。自2010年以来强加给雅典的结构调整计划不顾对其大部分经济及公共服务造成破坏的代价,已被证明无效。
本人以及我们在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团队所进行的工作表明,在一个像日本那样可以控制本国货币的国家[17],在判断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时,没有单一的门槛,而是必须考虑一系列参数:例如,工资在GDP中的比例越高,失业率越低,私人债务也越低;此外,一个国家可以容许自己承受高额公共债务,前提是为必要的公共投资融资[18]。
多年来,法兰克福的中央银行自认有权通过保持非常低的基准利率来制造大量流动资金,因为这种货币政策似乎没有导致通胀的影响,然而,事实上,通胀隐藏在房地产和金融泡沫中[19]。现在,欧洲央行仍坚信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了通胀,因此想排干自己一手制造的洪潮。问题是,由于不再被人为操作压低,欧元区国家公共债务的利率立即开始飙升,向欧洲公共财政和通胀实际状况的水平看齐。德国已经恢复到接近+1.5%的利率,而意大利则已接近+4%。欧元区国家的借款利率达到通胀水平加上风险溢价(这取决于金融市场对一个国家偿付能力的评估)是合乎逻辑的,这应该使它们处于8%(德国)和12%(意大利)之间的范围。尽管金融市场用来评估主权债务偿付能力的标准往往不具备科学依据,但这样的利率水平将不可避免地加快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增长速度。这个循环将自我延续,以至于一些投机基金(它们没有受到任何为保护我们的公共财政而采取的行动的干扰)将选择以某一欧洲国家不偿还债务为赌注,就像它们已于2010年以希腊为代价所作的那样。
因此,一个具体存在的风险是,金融崩溃——债券世界或股票世界,甚至两者一同——或是将与欧洲公共债务危机相伴而来,或是随之于后。因此,欧洲央行面临着第二个微妙的困境:要么继续购买那些可能承受不起利率上升的国家(首先是意大利)的公共债务,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将继续助长通胀,而且很可能会遭到德国的反对;要么放弃向那些公共财政显得很脆弱的国家(无论是对还是错)提供支持。我们将不能再指责它为通胀火上浇油,但对意大利来说,一旦金融市场感到畏惧,我们可能将不得不实施类似于对希腊实施的程序:将其置于三驾马车的监护之下,实施一项将摧毁意大利经济的紧缩计划[20],随后将对其很大一部分资产(机场、公共公司、岛屿、港口等)进行私有化。然而,希腊的情况告诉我们,这些“秘方”并不能降低债务与GDP的比率:在破坏经济的同时,紧缩措施至少会像债务一样迅速地削减GDP。然而,罗马不同于雅典,可以假设,由此产生的政治混乱可能导致它退出欧元区。欧洲央行试图避免的正是这种负面情况,这也是它迟疑的理由:7月份它只将基准利率提高了0.5个点,同时宣布结束扩大资产购买计划(App)和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还计划实施Tpi(传输保护工具)方案,授权无限制地回购政府债务。然而,为了逃避助长通胀的批评,Tpi设想欧洲央行将不会发行新的流动货币,而只是将其从偿还旧债中收回的资金重新投资。大家都很清楚,这实际上将大大限制欧洲央行的执行权力,而像Ubs这样的银行已经公开批评了这一机制的无效性。
最后还有一个想法是在未来实施数字欧元,即欧洲央行发行的加密货币。据其发起人声称,这将允许任何欧洲储蓄者为欧洲主权债务提供担保。然而,三个反对意见是:1)加密货币需要大量的能量来运行其加密算法。这将是一个严重的生态学错误。2)不需要一个数字欧元来允许欧洲公民将他们的储蓄借给国家。在法国,以前每个人都可以认购国债,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做法被禁止,以迫使国家向市场融资。3)多年来,欧洲银行一直热衷于向数字欧元转型。为什么?这将允许他们集体对欧洲储蓄者的存款账户征收昂贵的管理费,而后者却无法通过提取资金来保护自己:他们无法将数字资金藏在床垫下。
事实上,“鹰派”北欧国家,包括德国、奥地利、荷兰、芬兰,至少从2016年开始就在准备一个协调退出欧元区并建立一个“马可区”的计划[21]。如果北欧国家从南欧国家中脱离出来,那么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法国很可能会感到不得不跟随德国进行这场冒险,为保持与莱茵河对岸的邻国保持共同货币,甚至会不惜抛弃意大利、牺牲欧洲计划并冒着成为“北方希腊”的风险。至此,是否可以看懂为什么我们的中央银行在最近的决策中没有任何“技术性”,反倒是取决于重要的政治决择?现在是对这些决定进行民主审议的时候了。
亦或如何?
然而,有许多方法可以确保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欧洲计划的可持续性。若详细介绍这些替代政策,需要远远超出本文所限篇幅的空间。因此,请恕笔者做概要性介绍。
依我之见,首先要做的是实行价格管制。这也是罗斯福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实行过的,即通过在1941年成立的价格管理办公室对消费品价格和租金进行控制[22]。当然,有人会说,我们(仍)未处于战争年月。对这一异议所需的回应是:实行生态转型、适应全球变暖和已经发生的生物多样性消失至少与战时经济的幸存一样紧迫。今年夏天,意大利南部和法国一些省份已开始对饮用水施行配给。据了解,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意大利将在2040年以内失去至少40%的淡水储备。全球变暖是一个比任何人类军队都要强大和持久的“敌人”。欧洲是否必须回到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下的饥荒,才能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此外,已经有人发声表示,我们正在经历的部分通胀并不是因为成本上升,而是由于“寄生虫”试图趁机牟取暴利[23]。这正是需要进行价格监管的地方。它不会消除因开采化石燃料和原材料成本上升而导致的不可压缩的通胀,但会大幅度限制其影响,例如,禁止超过20%的利润率。如今,价格监管似乎被视为一种中世纪或者说是朝鲜模式,因为我们的思维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塑造而成。在法国,倒是像雷蒙·巴雷(Raymond Barre)这样的自由派财政部长曾经实施过价格监管。这毫不稀奇。
然而,一旦意识到目前通胀主要由获得越来越稀缺的化石燃料(首先是石油)及某些原材料所决定,那么显而易见的应该是,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其害的最好方法是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有些方案寄希望于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并使我们的经济去碳化。本人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以法国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证[24]。当然,这种愿景的成本(2050年前每年占GDP的2%)肯定是不容忽视的,但对像法国这样仍然繁荣的经济体来说仍然可以承受。减少我们的经济对某些注定会变得稀少的自然资源的依赖,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虽然并不亚于去碳化,却不那么容易理解:其中包括放弃我们的产品小型化、生活微电子化以及计划性报废“一次性产品”。它需要发明一个低科技工业来生产既耐用又便于维修和回收的产品。
得益于控制价格和减少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然后尽快减少对关键矿物的依赖),在将通胀率恢复到可承受水平(2%至4%之间[25])之后,中央银行将不再需要提高利率或结束其购买政府债务的政策。至于像意大利或希腊这种处于困境的经济体,与其通过Tpi,不如通过新的欧盟债务发行来资助它们,可能会更有效,就像2020年发行的新冠债券(coronabonds)。当然,前提是偿还这笔欧洲债务的资金来自于新的税收收入,比如在欧元区边界征收碳税或是对金融交易征税。尽管如此,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从根本上促成了投机泡沫膨胀和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货币洪潮政策?在我看来,这是行不通的。各中央银行应该调整其货币政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转型前景融资:一个名副其实的绿色新政,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26]。央行可以,比如说,将实施这种绿色转型计划设定为购买政府债务的前提,而且,以商业银行信贷政策的“生态化”作为调节其基准利率的条件[27]。
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样的政策将没有理由助长通胀——这与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而是将继续注入货币:这一次是将其注入实体经济,而不再是金融市场。
让我以下面这个作为整个审查基础的经济分析要素为结语。一般价格水平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指流通中的货币量和实体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28]?如果货币量增加而蛋糕不增大,即不创造价值,那么是的,的确会发生通胀。这就是我们每天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所观察到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蛋糕增大的速度与用以衡量其价值的货币量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那么就不可能发生通胀。这就是一些国家能够在没有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实施巨大投资计划的缘由。难道真的担心一个名副其实的绿色新政不会创造足够的经济价值来避免通胀的螺旋式上升吗?答案当然是不确定的,我们可予以承认。此外,每个国家的情况也各不相同。
但是,如果绿色新政能让我们既避免生态灾难的最坏后果,同时又避免只要我们依赖石油和其他矿物资源就会持续的滞胀,以及另一场金融崩溃和新的欧洲公共债务危机,这个风险难道不值得承担吗?一个在国际范围内协调的绿色新政如今还必须考虑到南半球国家农产品通胀可能导致的全球粮食危机。因为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西方央行的利率上升无助于抗击正在发出预警的饥荒。
- 具体地说, 2022年7月21日,欧洲央行宣布将参考利率上调0.5个百分点:参见https://tinyurl.com/34kdreuh ↑
- 也有一些罕见的例外,比如瑞士,其年通货膨胀率至今仍未超过3%。 ↑
- 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十年来,西方和日本的实际工资增长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缓慢。 ↑
- 参见Banca Mondiale, Indice dei prezzi dell’energia. ↑
- 参见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OECD, 2010. ↑
- 参见V. Court – F. Fizaine, ‘Long-Term Estimates of the Energy-Return-on-Investment (EROI) of Coal, Oil, and Gas Global Productions’, in Ecological Economics 138 (2017) 145-159. ↑
- 同样,经美国宇航局和美国国防部确定,可能阻碍美国军队在当前十年内完成任务的两个原因之一是停电(大流行病是第二个原因):参见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for the U.S. Army, 2019。关于一个以符合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的方式考虑能源和原材料的经济模式:参见G. Noel – G. Giraud – Ch. Goupil, «Modelling the Economy as a Dissipative Structure»,即将出版。 ↑
- 1980年3月和12月,美联储时任主席沃尔克在短期内将利率提高到了20%,以控制两位数的通胀率。 ↑
- 参见Rawi Abdelal, Capital Rules.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Fin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参见G.Giraud – T. Kockerols, Making the European Banking Union Macro-Economically Resilient: Cost of Non-Europe Report, European Parliament, 2015. ↑
- 参见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October 2016. ↑
- 参见Institut Rousseau, Actifs fossiles, les nouveaux subprimes? Quand financer la crise climatique peut mener à la crise financière, 2021. ↑
- . 作为比较,法国国家的年净收入约为2400亿欧元。 ↑
- 这既是因为中国政府更乐于将其再投资于国内市场,也因为中国与西方贸易现在已几乎趋于平衡。 ↑
- “庞氏骗局”是一种欺诈性经销模式,由查尔斯·庞氏(Charles Ponzi,1882-1949)缔造,它向早期投资者许诺高额回报,却不顾新投资者的利益,而是使他们充当骗局的受害者。 ↑
- 参见C. Reinhart – K. Rogoff,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2010/2) 573-578。罗格夫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莱因哈特(Reinhart)是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
-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95%的主权债务持有者是日本公民,如有必要,日本央行可以为国家再融资。欧元区国家的情况已不复如此,它们发行货币的权力已被剥夺,并被委托给一个独立的机构,即欧洲央行。此外,例如法国60%的公共债务和意大利30%的公共债务为非居民所持有。 ↑
- 这证实了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就国家企业这一主题所捍卫的论点。 ↑
- 令人遗憾的是,在计算欧洲央行的通胀目标时,金融和房地产资产的价格未被纳入考虑之中。这种“疏忽”不具备任何科学依据。 ↑
- 自2010年来,强加给希腊的结构调整计划使其损失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破坏了经济,并导致大部分公共资产私有化,而未能以任何方式解决公共债务的“问题”:公共债务至今仍然占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80%,与2010年相等。难道这就是当初的真正目标吗? ↑
- 本人于2016年从奥地利中央银行行长处得知这一秘密计划。 ↑
- 30,000名雇员被国家复苏管理局录用,以监管全美国的消费价格发展。在法国,价格控制在其海外领土上完全合法,并通过公共当局、企业及用户之间的协商正常实施。 ↑
- 法国最大的零售连锁店之一的负责人Michel-Edouard Leclerc在2022年6月30日接受BFMTV采访时,呼吁成立一个“通货膨胀起因调查委员会”,因为据他所言,“制造商提高价格的要求中有一半是不透明的,恰恰相反,是可疑的”。参见https://tinyurl.com/mru88sty ↑
- 参见Institut Rousseau, 2% pour 2°C: Les investissements publics et privés nécessaires pour atteindre la neutralité carbone de la France en 2050, 2022. ↑
- 早在通胀回升之前,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就曾提议将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提高到4%。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建议。2%的门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的,当然,前提是工资和养老金要与通货膨胀率挂钩。 ↑
- 在美国,拜登政府终于使《减少通货膨胀法 Inflation Reduction Act》获得通过,这将使为能源转型的一些基本工程提供资金成为可能。但是,即使政府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的、雄心勃勃得多的3万亿美元《重建更好 Build Back Better》草案,也已然是桑德斯团队最初构想的7万亿美元《绿色新政 Green New Deal》的缩减版。 ↑
- 许多其他激励措施可通过金融部门得以实施。恕不在此详述。参见G. Giraud, Transizione ecologica. La finanza a servizio della nuova frontiera dell’economia, Bologna, Emi, 2014; Id., La rivoluzione dolce della transizione ecologica,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 Ed. Vaticana, 2022. ↑
-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这只是一种简化,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E. Dossetto – G. Giraud, «Monetary velocit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stock-flow consistent dynamics», in Environmental Justice Program’s Working paper,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