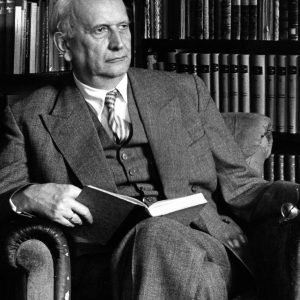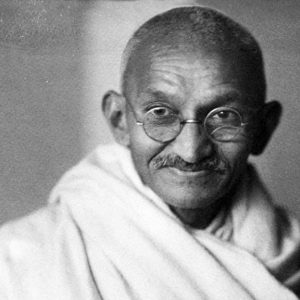什么是美?
什么是美?它是主观的、相对的吗?美通常被视为只是愉悦的简单同义词,因此说某样东西是美的,似乎是说它令人愉悦,至少对某些人而言是这样。这样一来,美就变成了一种纯粹主观的东西,取决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感受方式、习惯和生活观念。
心理学研究则表明,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对某物或某人的“美感”评价非常相似。美感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而非后天习得的,它自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六个月大的婴儿就能清楚地表现出他们对面孔的吸引或厌恶,以及他们的偏好,这些喜欢的面孔在后来的年龄段中仍然被评判为美丽的:”儿童和成人表现出相似的判断标准。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存在着非习得的美标准的存在[…]。我们对人的美丑的判断不受环境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吸引力的人的照片,我们并不会因此倾向于提高我们的判断标准。反之亦然”[1]。这些结论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2],从而推翻了一个普遍的说法。
但是否可以具体说明是什么让某件事或某个人变得美丽呢?古人将美与整体和部分之间的 “和谐 ”和 “比例 ”联系在一起,这可以从雕塑(如波利克里图斯雕像)和建筑(如帕台农神庙)中看到。这种和谐与比例可以用所谓的 “黄金分割 ”来表示,即一个线段的总长度与其部分之间的比例,具体表现为一个介于 0.618 到 1.618 之间的数值范围。适用于建筑的方法同样适用于面孔,当面孔展现出这一比例时,就会被认为是和谐而美丽的。
古人的直觉一直延续至今,证明了美的本质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是毫无艺术性可言的物品,如磁卡和信用卡,其设计也遵循了具有与黄金分割相同的比例。对来自不同文化和地理归属的受试者中进行的关于美的感知、建筑美感和更广泛的艺术美感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崇高之美的模式似乎带来了更强烈、更愉悦的审美体验,不仅对专业的观察者如此,对普通人亦然。”[3]。
美的多重特性
在古典和中世纪的哲学反思中,美虽然不在所谓的 “超越性 ”之列,即不在作为存在的本质属性(一、真、善)之列,却通常与它们联系在一起[4]。事实上,尽管美并不在上述清单之列,但它却能以最引人入胜的方式表达生命的这三个基本方面,因为它具有一种独特、崇高却又极其具体的吸引力。
事实上,美与感性有关,但同时又具有强大的象征性提示作用:它所呈现的价值和理想之所以吸引人,正因为它们是美的。同时,所见所闻又暗示着另一种信息,这种信息越是含蓄,越是难以言喻,就越令人着迷,就像邀请人们踏上一条未知的征程,但却能让人心潮澎湃,进入一个不同的维度。
此外,由于美与感官有关,首先是视觉,美不仅与情感有着特殊的关系,而且也与肉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美具有复杂的特殊性,能够同样引人注目精神和肉体;美的两根支柱牢牢地支撑着存在的两个维度:肉体和精神。它们那脆弱的平衡表达了美的那种永远难以捉摸的神秘及其具象价值的特征。由于这种复杂性,美总是处于不稳定和永不确定的状态,因此美能够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述说神性,同时又能为人类经验所触及。
希腊世界除了通过其宏伟的艺术作品明确美的尺度外,还将其作为引人深思的对象,认为它首先是超感世界向人类发出的呼吁:超感世界通过触动心灵的迹象,以审慎的方式让人们了解它,点燃对某种曾经体验过、感受过的圆满的渴望。
在柏拉图看来,美与爱欲(Eros)有着特殊的联系,爱欲的任务是吸引人走向至高的现实。爱欲被定义为精灵,即介于人类与神祇之间的中介者,是两者之间沟通的桥梁:”爱欲是一个巨大的精灵:事实上,所有精灵都站在凡人与不朽之间[…]。站在神与人之间,他完成了一切,使整体与自身紧密相连。[…]神不会与人混杂在一起,但通过这位精灵,神与人有了各种关系和各种对话,无论是在人醒来时还是在人入睡时”(《会饮篇》(Simposio),202 E – 203 A)。再想想《斐德罗篇》(Fedro)中著名的御车人形象,爱欲被刻画为御车人(灵魂)必须驾驭和指挥的一匹马,以便顺利地驾驭战车。对柏拉图来说,爱欲具有这种超越性的因素,是通向神圣的途径。在这场掌控灵魂的艰苦斗争中,如果灵魂找到了通往天堂的道路,它就可以被驯服,被 “驾驭”,而这正是美德的关键所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天主–至高无上的美–以爱吸引着人,使人参与到祂的幸福中,尽管只是暂时的:”美与一切本身可欲望的事物也在同系列之中[…]。宇宙自然与诸天就依存于这样一个原理。而我们俯仰于这样的宇宙之间,乐此最好的生命,虽其为欢愉也甚促,而在那个状态下,祂始终是存在”(《形而上学》,第十二卷, 第七节, 1072 a 34 – 1072 b 13-17)。尽管批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最终还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他而言,艺术本质上是对真实的模仿,是诗歌和戏剧表现所特有的存在的真实性。此外,艺术具有教育和培养人们认识真善美的能力,这得益于美的 “循环 ”概念将美与存在的其他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参见《诗学》,1448b)。
普罗提诺(Plotino)重述了希腊古典主义的思辨历程,并使其臻于完美。在《九章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著名的美学论著之一,正如此前所述,它是对“绝对者”的参与,智者被邀请参与到苦修之路中,就像雕刻一尊雕像一样,这是必须的修炼,因为只有这样,内在的灵魂之美才能显现出来:”回到你自己身上看一看: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自己内在的美,那就像雕刻师那样去做,雕刻一座必须变美的雕像。他去除、刮削、打磨、清理,直到美丽的形象在大理石中显现出来:像他一样,你也要去除多余的部分,拉直倾斜的地方,净化阴暗面并使其光亮,不要停止雕刻自己内心的雕像,直到美德的神圣光辉显现出来,直到节制坐在神圣的宝座上[…]。眼睛如果不是像太阳一样,就永远不会看到太阳;灵魂如果不是美丽的,也不会看到美丽。因此,如果每个人都希望默观天主和美,那么他首先要成为有神性和美的人”(《九章集》,第一卷, 第六章, 第九节)。美,通过艺术感知,吸引人们进入超感性的维度:通过美,人可以在时间中体验永恒。
因此,在美中灵魂与肉体的两极性表达了天与地、肉体与灵魂、时间与永恒、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双重张力关系。即使是看似最平凡和痛苦的经历,也显示出这种张力,并伴随着以不同方式发挥潜能的希望。正因如此,古人将美视为美德的反映,是灵魂圆满状态在感官层面的体现:“正如身体上有一种和谐匀称的特征,与美丽的肤色结合在一起,这就叫做美,对于灵魂来说,意见和判断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与某种坚定性和不变性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美德的结果,或者说包含了美德的本质,这就叫做美。”(西塞罗,《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第四卷, 第十三章, 第三十一节)。
美吸引着人们走向神圣,实际上这是它最恰当的名字之一:它是神圣的起源和稳定性的保证。 实际上,由人创造的美丽,即使是最迷人的,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它表现出人对意义和永恒的渴望,这也是对参与永恒之美的诉求。
美的 “民主 ”维度
美还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能够吸引和迷住每一个 “敏感 ”的人(即具有感官的人,如果这些感官受到培养,也表现为感受力),无论他们的生活观念、经济和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多么不同。同时,正如人们多次注意到的那样,它能够表现出感官所感知之外的 “另一个”世界,为人们打开一扇通往无形之境的大门,艺术家成功地赋予了其形式、声音和言语,而这一切大多只是对它的影射:通过它,无形变得有形。美能够激发人的心灵,但又不是强制性的;它引发人的智慧、自由、情感与意志的回应。
这就是所谓的美的 “民主 ”特性,因为它呈现为一个对任何人都有吸引力的目标,能够将持对立思想立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在面对被视为美的事物时感到惊叹:”人类通过无数条道路,从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出发,来达到艺术的境界。美学史表明,艺术家们在不同时期受到迥然不同、互不相容的艺术观念的影响,尽管这些理论相互矛盾,他们仍然创造了艺术作品,这并不表明这些理论无关紧要,而是表明艺术是一种现象,尽管它建立在当时的文化和知识秩序之上,但最终还是要超越逻辑论证加以探寻”[5]。即使是那些试图拒绝艺术的人,也无法完全摆脱它,至少在表达自己思想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它。
在这一点上,柏拉图依然堪称典范。在《理想国》第十卷中,他严厉批评诗歌和神话,因为它们被认为是 “模仿的模仿”,因为艺术模仿事物,而事物不过是理念–真正的现实–的影子。然而,当柏拉图必须谈论最高的真理时,他依靠的不是逻各斯(logos)的严谨,而是图像和叙述的感召力,在这些图像和叙述中,我们或许能找到他最高和最动人的篇章。想想洞穴的神话、灵魂的疯狂逃亡、《斐多篇》(Fedone)结尾的木筏、《斐德罗篇》(Fedro)的有翼战车。可以合理地说,柏拉图虽非有意为之,他也是一位艺术家,因为艺术占据了他,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学一样,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对整体的批判性理解,这种理解是每一个陈述的前提(参见《形而上学》,第一卷, 第一章)。同样,在谈到美时,艺术以光辉和吸引人的形式所展现的特有的和谐统一的能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即使一个人不想承认艺术价值,他也会发现自己像柏拉图一样,甚至不由自主地与“引向他处”的力量抗争,无论这力量是否符合自己的信念和观点:”艺术家就是这样超越了他的哲学、意识形态和实践信念,艺术是一种摆脱他自己控制的东西,超越了他的意图和计划。但丁在表达他的诗歌时,将其根植于中世纪的世界观,基于他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天文学、科学甚至占星术,因此也基于神学。卡夫卡几乎无视但丁的整个宇宙,反而创作出植根于他的时代及其世界观的崇高艺术作品[…]。由此可见,艺术作品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跨越意识形态的藩篱、实际的心理分隔、利益的壁垒,不顾创作者、阅读者、观赏者和倾听者的意图,将自己融入人类现实中无法控制的空间,在那里,一切都在质疑之中,一切皆有可能[…]。像唐·阿邦迪奥(Don Abbondio)这样自私自利的傻瓜和唐·吉诃德(Don Quixote)这样的疯子变得可读,因此也变得无限可爱,因为他们被认识不是因为他们所指向的,而是因为他们存在本身”[6]。
美的超越性
由此可见,艺术美具有超越性,不受任何理论框架或占有欲的限制。艺术美是一种超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蔑视它,任何人都可以被它的魅力所吸引[7]。即使是被体制或党派奴役的艺术家,也会很快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致命的十字路口:要么为意识形态服务,要么让自己被艺术灵感所引领,却不知道它将把自己带向何方。为权力辩护的作品在美学上总是平庸的(现实主义艺术就是一个例子,苏联和法西斯的现实主义艺术在诞生之初都是备受赞誉的,但突然间就被人遗忘了)。而当艺术真正出众时,却会给既有政权造成冲击: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故事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
正如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指出的,艺术表现需要自由和不可捉摸性;它是颠覆性的,因为它神秘而不可预测;当人们试图将艺术表现奴役于生活和精神(即作者所称的 “事物的神圣性”)之外的 “其他”内容时,艺术表现就会退化和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作者并不自称为宗教信徒,宗教性,即 “事物的神圣性 ”所展示的视野,对艺术至关重要:“只有凭借其所代表事物的神圣性,象征才能保持其情感价值:当象征主义从纯粹的宗教领域转向纯粹的道德领域时,它就不可逆转地退化了”[8]。
但是,即使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作家内心也会体验到不可能将灵感封闭在预先设定的方案和框架中。当他尝试这样做时,他的内心就会产生反抗:“我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一个自由地屈从于哲学体系的诗人:卢克莱修(Lucrezio)就是这样对待伊壁鸠鲁主义的。他对该派哲学的捍卫,深有感触并付诸实践,使诗歌得到升华而非贬低,并与诗歌融为一体。然而,卢克莱修也时常失去他的纲领,使诗歌超越了纲领:《物性论》(De Rerum Natura)一诗,不是用伊壁鸠鲁主义征服灵魂宁静的赞歌,而是躁动不安、绝望的戏剧,是死亡噩梦的再现:正是诗人想用诗歌驱除的东西”[9]。
在萨特的作品中也能感受到类似的东西。尽管反复声明支持自由主义宣言,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萨特的笔下却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寒意,作者极力想让这种寒意复苏,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身体反抗将自己视为绝对,或被视为单纯的享乐对象:”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会意识到,尽管第一批演员在舞台上激动不已,但背景却不可抗拒地占据了上风;尽管为重新唤起欲望之火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寒冷依然在渗透和延伸。在萨特充满激情的肉体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最终不是绝对的自由主义主体,而是大写的非人格化力量,肉体、邪恶、命运、死亡,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新约》宇宙论和人类学中的’主宰'”[10]。
自由主义诞生之初是对生命的赞美,但事实上却变成了虐待狂,成为焦虑无法捕获梦寐以求的猎物的受害者,最终堕落为暴力和死亡,以表达对单纯享乐的不满。最终,“石头客人”令人不安地出现了,就像《唐璜》中的情节一样[11]。
伟大的作家谦虚地承认,如果他想描绘一个角色,他必须给角色自由空间,必须 “让他自己活出来”,将他与自身和他的想法分开:”角色是作家的创造,他们的存在、行动和言语都依赖于作家;反过来,小说家也依赖于他的角色,必须尊重他们。一些作家解释说,他们如何在内心倾听角色的对话,仿佛他们更像是观众,而不是作者;矛盾的是,他们倾听着自己的想象力说话。一位小说家对我说,他不得不让他笔下的一个角色死去,因为他的力量越来越大,有可能吞噬整部小说[…]。没有人像皮兰德娄(Pirandello)那样描述过作者心目中角色的成长:不是作者在寻找他的角色,而是 “六个角色” 在寻找他们的作者,以便能够生活、行动、说话[…]。福楼拜的回答很有名:‘包法利夫人就是我’”[12]。
这也是但丁在描写《地狱篇》时的经验:在描写那些被判处永恒惩罚的角色时,尽管他希望他们再次经历这样的惩罚,但同时又展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和伟大。想想《尤利西斯》和那篇著名的《知音》悼词,或是对保罗和弗朗西斯卡那温柔动人的爱情描述,或是乌戈里诺伯爵“高贵的骄傲”。就像在皮兰德娄的作品中,当一个角色以巧妙而成功的方式被描述出来时,他就会获得超越作者意图的特性和自主性;作者最终发现自己不得不被他笔下的人物牵着鼻子走。否则,这些作品将只是作者观点的简单延伸,或者只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或展示台,但绝不会成为诗歌、叙事和艺术。
这种艺术家“放手”自己作品的能力和必要性——仿佛为它们哀悼、任其自由发展,而非强行把它们囚禁在某种既定结构——正是所谓的“艺术的伦理性”。它在这种“放手”和放弃占有中找到了自己的真理。艺术家由此体验到灵感对自身的超越,灵感向他展示了一条未知且不可预测的道路:他只有让自己一步一步地融入其中,才能发现它。
- M. Costa – L. Corazza, Psicologia della bellezza, Firenze, Giunti, 2006, 5. ↑
- 参见 J. H. Langlois et Al., «美的格言还是神话? 荟萃分析和理论综论», 载于心理学公报, vol. 126, 2000, 390-423; B. G. Bardy – R. J. Bootsma – Y. Guiard (edd.), Studies in Perception and Action III, London, Routledge, 1995, 389-392; E. Hatfield – S. Sprecher, Mirror, Mirror…: 外观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M. S. Mahler, «论分离—个体化过程的前三个阶段», 载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53 (1972) 333-338. ↑
- M. Vannucci – H. Mühlmann, «崇高的建筑。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旅程», 载于当代心理学39 (2012) 57. 参见 M. Livio, La sezione aurea. Storia di un numero e di un mistero che dura da tremila anni, Milano, Rizzoli, 2017. ↑
- Tommaso d’Aquino riconduce comunque esplicitamente la bellezza a una caratteristica propria della bontà, intesa come armonia tra il tutto e le parti: «Il bene e il bello nell’oggetto sono la stessa cosa, poiché sono fondati sulla stessa cosa, cioè sulla forma» (Sum. Theol., I, q. 5, a. 4). ↑
- C. Lapucci, Estetica e Trascendenza, Siena, Cantagalli, 2011, 10. ↑
- Ivi, 10 e 50; corsivo nel testo. ↑
- 参见 G. Cucci, »La bellezza, via all’Assoluto, « in Civ. Catt. 2024 II 547-558. ↑
- J. Huizinga, L’autunno del Medio Evo, Firenze, Sansoni, 1966, 291. ↑
- C. Lapucci, Estetica e Trascendenza, cit., 11. ↑
- L. Lombardi Vallauri, Corso di filosofia del diritto, Padova, Cedam, 1981, 607 s. ↑
- Per un approfondimento di questa tematica, 参见 G. Cucci, Il fascino del male. I vizi capitali, Roma, AdP, 2012, 287-296. ↑
- L. Alonso Schökel, La parola ispirata. La Bibbia alla luce della scienza del linguaggio, Brescia, Paideia, 1987, 73 s. 还值得引用皮兰德娄的著名篇章,他在其中描述了他与笔下人物的关系:”我精神的创造物,那六个人已经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不再是我的生活,我再也无力拒绝他们的生活。以至于当我坚持要把他们从我的精神中驱逐出去时,他们却几乎完全脱离了所有的叙事支持,他们是小说中的人物,奇迹般地从包含他们的书页中浮现出来,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 他们会利用我一天中的某些时刻,在我工作室的孤独中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现在,一个或另一个,或两个一起,会来诱惑我,提议表现或描述这样或那样的场景,从中可能获得的效果,某种不寻常的情况可能引起的新兴趣” (L. Pirandello, Maschere nude, Milano, Mondadori, 1930, I, 7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