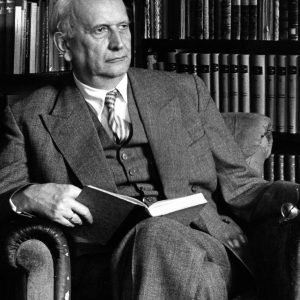导言
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已经意识到21世纪将是一个真正的“亚洲世纪”。同时,亚洲基督宗教社团的活力和创造力也日趋明显。另一方面,基于亚洲神学在过去三四十年中的基本原则和特征的发展,亚洲神学家试图将亚洲人民实际经验的本质归纳总结为一种“和谐神学”。为此,通过亚洲主教团协会(Fabc)组织的各种会议汇聚在一起的天主教神学家,为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将试析这种神学的独特背景、风格和主题,并结合其中存在的区别,展示它对促进亚洲及其他地区教会、神学和灵修发展产生的影响及其不断增长的趋势。
亚洲神学的背景:在充满反差的浩洋中航行
在初试构建和谐神学时,观察者应考虑基督宗教在亚洲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我们不妨将这种情况比喻为一个“充满反差的浩洋”:尽管各种环境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但最终被亚洲地区和伦理道德中的某种凝聚性潮流结合在一起。
从宗教文化角度来看,亚洲拥有丰富的可汲取资源。中国文化包括道教、儒教和大乘佛教传统;印度拥有印度教和小乘佛教,以及其他直接来自印度半岛的宗教表现形式;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另外还有遍及全亚洲的土著信仰和各种常常与其他宗教表现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各种习俗;最后,还有最早产生于西方的基督宗教。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亚,基督宗教早在16世纪前就已经存在。事实上,自六世纪以来,在波斯商人的帮助下,叙利亚教会就已于古锡兰、缅甸和马来群岛建立。
在欧洲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基督宗教,自1550年以来由东北部传入亚洲,与日本、中国和韩国文明相遇。然而,直到最近几年,本土资源和见解才被明确地运用于神学工作中。例如,上海的耶稣会神学院在1952年至1967年之间移至菲律宾,直到1964年,一贯使用的唯一教学语言才由拉丁语改为英语。在天主教环境中,直到1968年在台北成立辅仁神学院之后,中文才进入教育和研究领域。从此之后,变化飞速且深刻。日本和韩国也发生类似情况。
基督宗教在亚洲环境背景下的语言和文化中扎根,这项工作有多方面的意义。这意味着对词汇、概念和语言结构中包含的世界观的再认识。为此,需要对词汇表达的多种体验持开放态度。我们不妨将加深本土化的基本条件称为“诠释性关注”。另外,为了更好地认识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挑战,敏锐和勤奋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最后,亚洲的基督徒还需要在政治问题上采取忍耐和宽容的态度,大觉醒运动1成为主要宗教趋势的现象常常有损于宗教的共存和宗教自由。
在对当地情况持尊重态度的前提下,强烈的亲身感受有助于亚洲神学家们对以上要素以及其他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关注时代的标记是神学使命的一部分。米歇尔·德·塞多(Michel de Certeau)曾经指出,“神学”(teologia)这个单词来源于theos(神)和logos(基于理性的系统论述)两个词的组合,这同时意味着它产生于logos和Kairos(天主临在的非凡时刻)之间存在的张力2。神学有助于对教友彼此之间分享信仰经历的分辨(参阅若一41-4),同时神学的语言和基本概念也必须根据天主临在的具体方式得以更新,延续救恩史的叙述。这个在整个基督宗教历史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如今在亚洲亦是如此。
神学的风格:心灵的乐观
神学不仅是一种话语,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首先,神学需要对其话语的实践方式进行批判性分辨,对进行过程中话语获得的认同是否得到肯定和传达做出评价。其次,真正的神学话语应基于天主圣言在团体中被接受和体现的形式。归根究底,神学旨在将经验转化为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基督宗教社团必须与创造神学风格同步进行3。
和谐神学的逐步发展揭示了亚洲基督宗教团体的典型“神学风格”,这一点在其诞生和巩固的历史中得到证明。从一开始,作为一个集体性创作,它的发展与亚洲主教团协会的作用密切相关。亚洲主教团与教宗保禄六世于1970年在马尼拉举行历史性会晤之后,亚洲主教团协会于1972年成立并得以发展,如今包括22个亚洲国家主教团,西起巴基斯坦,东至菲律宾,北到韩国,南达印度尼西亚。
到2015年底,亚洲主教团协会文告中已收纳147个题目,是一个共建教会和神学的重大集体成果4。长期以来,协会举行各种神学活动开展不懈的研究,努力促进面临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挑战的国家之间达成更深入的共享和共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神学取得卓大成效的时代。尽管一些神学家对亚洲和谐神学的形成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同样必不可少。这个特殊的神学努力不是任何人的特权。它的形成过程反映了建立在其认识论基础上的价值观和方法,换言之,“方式不能脱离宗旨。对完美的追寻意味着追寻的方式也要完美”5。
在构建对话和共识的基础上,和谐神学努力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了这些基本价值观。亚洲主教团协会完全赞同《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Nostra aetate)确立的对话观念,并规定:“对话是在亚洲福传的方式”6。在1974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协会宣布了关于在福传使命中推崇三个对话的声明:“与亚洲穷人进行对话(为穷人提供解放和选择权),与他们的文化进行对话(本地化),与他们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进行对话(宗教对话)”7。
这三个对话启发了此后大多数文告的问世。亚洲主教团协会的这些文告提出了和谐神学的基本概念,发展出与“对话”紧密联系的“亚洲”神学风格。
潘尼卡曾对这种方式的认识论基础加以概括:“辩证法通过对事物顺序、理性的价值和有说服力的论点的信任寻求真理,同样,对话通过对他人的信任达到真理。如果说辩证法对理性抱乐观态度,那么对话则是心灵的乐观者。辩证法相信可以通过在概念上达到客观性一致来寻求真理,对话则认为交流双方的主观性一致有助于他们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前进。最重要的是,对话不是两个不同论述之间仍处于辩证状态的争论,而是两个论述在共同寻求真理的道路上的一种超越”8。
印度慈幼会神学家Jose Kuttianimattathil试图系统地描述印度/亚洲对话方式的特征。“对话的进行方式是使某人能够通过对其他宗教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研究、反思、祈祷和沉思,并与自身团体的信仰互动,从而进行自我纠正、充实和改变,甚至对他人提出挑战。(…)与其他神学方法一样,对话方式只能从引起对话的神学中进行验证。如果对话能够在宗教多元化环境下忠实地描述基督宗教信仰的内涵,并且基督宗教团体能够对自身信仰的这种描述予以认同,那么它便可被确定为可行的方法”9。
符号和故事
和谐神学的“神学风格”具有另一个典型特征:加倍着重运用图像、比喻、诗歌和故事等历史上惯用的精美语言形式彰显天主。
印度神学家Francis Gonsalves将天主神国视为一个“反空间”,推翻了我们设立的神圣/世俗、内部/外部等一系列有关空间概念的分类10。他将和谐描述为一种在这种环境中进行的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整个村庄共同参加的团体性舞蹈:“这是用舞蹈重新诠释生活。也就是说,生活是团结与共融的舞蹈”11。
我们也可以将这个比喻扩展到对三位一体的反思,因为“舞蹈的动力激起的是多种表达形式融于一体的统一表现”12。基于生活经验的比喻开辟了一个将真实人类与真神结合在一起的空间。
什么是和谐?“和谐”是一个覆盖面极广的词,因此有时含义似乎不甚清晰。亚洲主教团协会的一份报告试图不将它作为“专业性”概念,而是为展示社会和精神世界的一个敞开的大门:“亚洲有一种看待现实的方法,它对现实的理解非常深刻。在这种世界观内,整体是关系网络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总和,其中不存在与其他部分不相关的部分,并且所有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每个部分的存在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可分割。为摆脱不谐调并追求圆满生活,我们必须汲取亚洲文化和宗教资源,促进当地各民族之间共融,并更有效地进行沟通”13。
其他文告则针对未来愿景方面对该词的含义发表了意见。他们指出,和谐首先是需要在生态问题上实现的理想;第二,在社会关系中,人的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否则不可能产生和谐;最后,和谐是实现多元化的一种方式,尤其需要努力加强不同宗教间的对话。
上述任务中的最后一项引起了许多亚洲神学家的强烈反响。有人认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宇宙合一”和“与万物和好”是天主的旨意,那么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相遇将必然带来更深刻的理解及和谐,并且自然而然地引领我们进入新的对话维度14。
中国基督徒自耶稣会士和中国文人开始认识彼此的传统著述以来,便致力于中西古文化经典著作的比较,他们非常擅长将儒家思想与圣经传统相融合。中国耶稣会神学家马克·房志荣(Mark Fang Chih-jung)在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表示,这部经典著作生动地记录了孔子及其门徒之间的对话,它描绘的“教育境界”同时向读者展示教与学双方的乐趣。同样,耶稣通过实际的、有时存在矛盾的学习经历,在祂的公共生活中带领门徒获得启示。这两种情况都同样是对世界和人类的本质进行的探索:耶稣将其扩展到关于天主奥秘的全部启示。这种经常出现在《论语》或《若望福音》中“道”和“门”的比喻,有助于我们对导师的谦逊态度的理解:因此而折服的门徒必将会跟随师父踏上正确的道路。
在中国环境背景中,孔子是为人之师的典范,是培养内在自由和不断鼓励修身养性的指路人。通过接受孔子的教育方式,中国基督徒可以更好地理解耶稣的道路深深扎根于人类本质和本性,并惊叹圣神在不同文化和各个历史时代中的彰显15。
和谐,正义,生态
将和谐理解为“舞蹈”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它也可能是“角斗”。Felix Wilfred和另外一些持相同观点的人指出,从亚洲方法对和谐概念的理解也需要我们把握它与社会问题和生态正义相关问题的关系16。和谐与有机团结有关,对这个概念和价值的支持要求我们致力于解决导致分裂的冲突和斗争。张力在不断更新的动态中产生,我们应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斗争都是为了恢复社会和宇宙的团结,因此必须以此为目标进行,决不能背离斗争的起因。
和谐神学不仅是教会的方式或一系列要做的事情。它努力探索,试图通过天主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团体中存在的方式,揭示祂就是在我们中间的最终奥秘。这些见解来自古老的经验,也是扎根于不同区域的基督宗教团体的见证。
最近,致力于宗教对话的亚洲主教团协会神学家强调,和谐神学需要见证:“我们宗徒团体以个人和团体生活的友爱,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为耶稣作见证。它们是沉默、临在和故事。在生存的沉默中,我们以克己和充满爱的心专注地聆听别人的声音,并回避妄加评论。在这种深沉的沉默中,我们意识到耶稣临在我们中间,启示我们宗教对话的旅程以及改变世界的行动。另外,讲述我们通过耶稣而转变的故事可以见证,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团,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将全球化的冷漠和消费主义文化转变成一种团结和分享的福音文化”17。
沉默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亚洲神学家所钟爱的论题之一。Aloysius Pieris做为典型代表之一,经常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话语与沉默之间的和谐是亚洲真实性的考据。圣神确是永恒的能量,使所有的话语从沉默中涌现并重归沉默;使一切承诺都因放弃而产生,一切争斗都来自安宁,一切自由都来自严格的纪律,一切行动都来自平静,一切“进步”都来自随缘,一切拥有都来自超脱。(…)如果我们的话语与沉默之间和谐相处,无论是在礼仪、服务或谈话中,那么圣神就在我们中间”18。
因此,亚洲神学家认为沉默和话语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彼此互为涌现,他们用音乐的比喻来进一步说明这种思考方式。Felix Wilfred对印度音乐典型风格的想法是在瞬间体验永恒的可能性。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克服我们在时间和意识上固有的直线式局限性:“(在印度音乐中),有一种永恒而和谐的旋律,不能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不能分为起点、中间和终点,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无尽的永恒,一种‘当下’的经历。尽管有机视觉基于与现实存在关联进行式的意识,但经验却并不以时间为首要条件。相反,一个人从他的意识的各种多样性和丰富性中寻求整体。因此,在人类意识中,许多事物可以同时并存和经历”19。
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韩裔美籍神学家Jung Young Lee从中国的和谐概念出发,结合阴阳哲学体系中“既是……又是”(而不是或是……或是)的世界观来思考“三位一体”的奥秘20。
新教神学家Heup Young Kim建议以“道”取代神学和信仰对话的两个基本替代性比喻,“知”(logos)和“行”(praxis),并将由此而来的范式称为“theo-dao”(道神学),既不是“theo-logos”(传统神学),也不是“theo-praxis”(解放神学)。他认为,logos和praxis这两个比喻仅强调“知”和“行”的一个方面,而“道”,正如中国哲学家王阳明所言,则是两者兼有的结合21。
在所有这些体验外在现实和内在世界的方法中,外在的行动和内在为改进自己而付出的努力实际上同属一个过程。孟子早已对此进行了解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22。
这种神学之旅基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表达的对外在和内心和谐的追求,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基督宗教主义方式,将耶稣视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复活的圣人”23。耶稣从降生成人到虚己(kenosis),与圣父深厚的团结成为互动和与外界互动的地方。耶稣基督将真理与生命结合起来,祂引领我们走的路是真正的“和谐之源”24。
问题与前景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和谐的主题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但仍不足以把握亚洲神学的多样性和微妙差异。例如,台湾新教神学家25倡议发展的“爱国”神学与传统文化在某些概念上的分歧难免会削弱或否认地方和弱势群体的情感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
在中国环境中,自称为“中国基督宗教神学”的思想以其他前提为出发点。他们以多方面因素为出发点进行神学讨论,结合许多与个人经验和母语相关的典型,在专业和非专业神学家之间展开。对于这些学者而言,“个体性”和“现代性”是比和谐更重要的因素,他们常常拒绝使用中国政府偏好的政治性“和谐”话语26。
在印度,达利特是统治阶层视为“秽不可触”的最底层贱民。达利特神学家与印度其他神学家的本土化尝试并不产生直接矛盾,但他们强调在压迫性宗教和文化系统中嵌入的结构性犯罪和欺骗行为27。
提出和谐神学的大多数人都充分意识到这个词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关于和谐神学的论述)(…)似乎是一种企图掩盖正在发生的事实并使受害者脱离斗争的尝试。这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站在世界上拥有权力和特权的人的一边,他们喜欢的是诸如‘和平’、‘和谐’之类的语言,而不是冲突与斗争的语言”28。
和谐神学的可持续性及其内在创造力将取决于关于对话的认识:在整个历史中,对话总会不断中止并重启。即使对话因暴力和误解的阻力而中断,我们为对话付出的努力总会构成时空上的非直线性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将对话起初和进行中的所有努力连接在一起。对话从来没有确切的起点或终点,而是一系列不完整的叙述依次出现,并很有可能会将苏格拉底、孔子、耶稣和佛陀的门徒联系在一起纳入对话对象。
最后,随着对话的打开,长期的持续性努力将促进各个“本地”社团之间的团结,使受益的对话者以开放态度面对扩展空间,继续保持这种有效益的对话。中断、重启和不测是对话中的固有问题,因此,对它们的关注将有助于亚洲和谐神学不断开启新的征程。神学家的共同职责之一是开发创造力和新颖性的潜力:“所有神学家都必须表达耶稣基督的创造力,祂对我们的救赎“舍己而神圣”,“神圣而舍己”29。
结论
目前,对于任何特别议题,亚洲神学家均需以“乐观的心态”作为努力的基础。和谐神学重申,在寻求与所有生物的关系时,如果我们努力体验并培养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有机团结,人类将“有能力认识天主”。这种亚洲神学寻求和谐的态度基于对话,同时从圣经文学和亚洲大陆富有活力的传统中寻求启示,它因此是神学仍在进行的不断探索与发展:通过叙事、符号和概念的叙述,悄然地表达和分享对无限上主的追寻。
参考文献
- 这个术语主要是指18世纪和19世纪在新教中发生的神秘性运动。
- 参见M. de Certeau, La debolezza del credere. Fratture e transiti del cristianesimo, Troina (En), Città Aperta, 2006年。
- 参见B. Vermander,《从民族志学到神学:当代上海的宗教社团与东亚神学的任务》,载于《韩国系统神学杂志》 39(2015)7-35。(«From Ethnography to Theology: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Contemporary Shanghai and the Tasks of East Asian Theology», in Korea Journal of Systematic Theology)
- 谨在此声明,亚洲主教的文件目的在于向广大公众传达亚洲专家的思想并对亚洲教会面临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但并不正式代表亚洲主教团会议本身的官方立场。
- A. Pieris, ),《神学中的“亚洲意识”》(«The “Asian Sense” in Theology»), J. C. England (ed.), 《当代亚洲神学》(Living Theology in Asia), Maryknoll (纽约), Orbis Books, 1982, 174。
- 亚洲主教团协会第十届全体大会(2012年12月),《亚洲主教团协会四十周年:应对亚洲挑战。福音新传》(Fabcat Forty Years: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Asia. A New Evangelization), 第5条。
- 同上。
- R. 潘尼卡, 《神话,信仰和诠释。现实三重奏》(Mito, Fede ed Ermeneutica. Il triplice velo della realtà), 米兰, Jaca Book, 2000, 243.
- J. Kuttianimattathil, 《宗教对话的实践和神学》(Practice and Theology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Bangalore, KristuJyoti Publications, 1995, 608 s。
- 参阅F. Gonsalves, 《我们的土地之神。被颠覆的的三位一体神学》(God of OurSoil. Towards Subaltern Trinitarian Theology), 德里, ISPCK, 2010, 185 s。
- 同上, 178.
- M. Amaladoss, F. Gonsalves《我们的土地之神……》序言, 引, XVI。
- 《亚洲基督宗教和谐观》(«Asian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Harmony»), 见亚洲主教团协会文件 75, 条. 3-4。
- 参阅M. Amaladoss,《合体与和谐》(«Syncretism and Harmony»),载于《超越对话》(Beyond Dialogue), Bangalore, Asian Trading Corporation, 2008, 153。
- 参阅房志荣,《基督徒看孔子与其门弟子的关系》,载于《道风》8 (1998) 197-208。
- 参阅 F. Wilfred, 《边缘:亚洲神学》(Margins: Site of Asian Theologies), 德里, ISPCK, 2008。
- 第六主教宗教事务研究所(Sixth Bishops’ Institute for Interreligious Affairs Bira VI),亚洲庆祝《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Nostra aetate)发布50周年纪念,结束文件, 2015年11月, 第 8条。
- A. Pieris, 《神学中的“亚洲意识”》(«The “Asian Sense” in Theology»), 引, 175。
- F. Wilfred, 《边缘:亚洲神学》(Margins: Site of Asian Theologies), 引, 131。
- 参阅J. Young Lee,《亚洲视野中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 in Asian Perspectiv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6。
- 详见H. Young Kim, 《基督与道》(Christ and the Tao), 香港,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2003年。
- 孟子, 7A4.
- 参阅J. Tan Yun-Ka, ),《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圣人:建立当代儒学基督论》(«Jesus, the Crucified and Risen Sage: Constructing a Contemporary Confucian Christology»),载于R.Malek(主编)《耶稣基督的中国面孔》(《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Christ》), 卷3b, Sankt Augustin, Nettetal, 2007, 1481-1513。另参阅B. Vermander, ,《今日中国天主教神学家眼中的耶稣基督》«Jesus-Christ as Seen by Chinese Catholic Theologians Today», 同上, 1421-1430。
- 参阅《在当今亚洲发现耶稣的面容:亚洲传教指南》(«Discovering the Face of Jesus in Asia Today: A Guide to Doing Mission in Asia»), 《亚洲主教团协会文件84》 (1999).
- 始于C. S. Soong (见下条参考书目注释)。
- 关于中国神学发展,包括“爱国神学”,参阅M. Nicolini-Zani,《近十年来中国基督宗教神学的发展:在本土化与语境化之间》(«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Last Decades: Between Indigenization and Contextualization»),载于《三脚架》(Tripod) 39(2009)31-54。关于中国基督宗教神学,李秋零,《对“汉语神学”的历史反思》,《中国研究》第22期(2007)54-67; Y. Huilin– D. H. N. Yeung(eds),《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在中国》(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纽卡斯尔,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06;参阅孙向晨《汉语神学的可能性:从“文化基督徒”到“基督徒学者”》,《中国研究》第24期(2009)35-44。
- 参阅, 例如, D. Rasquinha, ,《婆罗门意识形态的达利特基督宗教批评》(«A Dalit Christian Critique of the BrahminicIdeology»), 载于《印度神学杂志》(Journal of IndianTheology)8 (2015) 23-44。
- F. Wilfred, 《边缘:亚洲神学》,(Margins: Site of Asian Theologies), 引, 121。
- K. Koyama,《富士山和西奈山,偶像评论》,(Mount Fuji and Mount Sinai, A Critique of Idols), Maryknoll (纽约), Orbis Books, 1984, 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