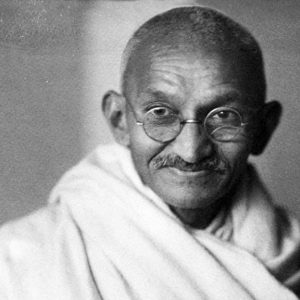第一位把“时代征兆”这个名词引入天主教官方词汇中的人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他在他1961年颁布的《人类的得救》(Humanae salutis)宗座宪章中说:“我们知道眼见这些邪恶实在令一些人心神沮丧,以致眼前看到的尽是黑暗,以为整个世界都已被它所覆盖,别无是处。然而,我们乐意重新肯定对人类神圣救主坚定不移的信心,祂未曾放弃祂所救赎的世人。的确,我们遵照主基督的告诫,祂规劝我们甄别‘时代的征兆’(玛16:3),在铺天盖地的黑暗中看出仍有许多迹象,似乎提供给教会和人类一个更美好的世代来临的预兆”(人类的得救4)。
一般来说哪些是时代的征兆?
从基督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时代的征兆有三个类别:原始的,常在的,个别的。基督降世这个事件整体来说乃是“原始的时代征兆”,也就是说所有其他的征兆都必须根据这个原始征兆来诠释。至于“常在的征兆”则有两种:受造物本身(它指出天主上智的安排)和人类历史的过程(它显示天主继续不断地临在其间);最后就是“个别的征兆”,它指的就是特殊历史事件,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为能确认并接纳这些征兆的真义,必须进行分辨。受造物本身和太平盛世时期可能比较容易彰显天主的圣意安排,但经历苦难时期通常要求我们对世态进行社会层面和个人内在的反思,这样的反思引领我们忏悔和净化自身。
为能认出时代的征兆,就需要了解圣神的用语,祂在时代的变幻中说不同的“言语”。这些言语可能是一阵微风,一道明亮的晨曦,或神圣的艺术家造物主以其最美好的方式把自己彰显在一片繁茂的绿野中。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可以在穷人的哀嚎中,在病患和临终者寂静的呻吟中,在被困移民的失望中,在遭受迫害的大众的反抗中,在备受剥削的大自然对生态被糟蹋而引发强烈反弹的现象中,或在我们内心深处感受到的重大催迫中,聆听天主圣神的呼唤。因此很明显地,在努力辨识圣神言语的过程中,默观和分辨的功夫必须辅以来自人文科学和信仰的洞察力。
有几位教父,如大巴西略,精修圣人马西莫和奥斯定,都极度重视解读受造的大自然,好能认出天主的智慧及其要传达给人类的讯息。教父们咸认为《圣经》和“大自然”是给我们揭示天主的两本“书”。
教宗本笃十六世也在世界和教会身陷的危机中发现了“时代的征兆”。他认为危机本身是痛苦的,甚至是残忍的,但也能是建设天国的良机[1]。此外,本笃十六世也使用“末世现实论”(realismo escatologico)的说法,指出上主永续的来临,对祂的来临我们必须以怜悯的行为来回应[2]。
我们可以从为了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而诞生的新神学、释经学、礼仪及信仰实践中,辨认出对“时代征兆”的某些回应。从另一方面说,这些新生事物的凸显也可以是“时代的征兆”,这个征兆表明圣神特定的行动。每个时代的征兆无不质疑彼时神学的内容、结构、结果和方法,也因此产生了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神学。
了解时代和历史
基督宗教信仰传统通常区分时间(chronos) 与时机(kairos)之别,认为时间乃正常的时态运转,时机则为“恩宠的时刻”或“实践的时刻”。然而,在天主决定藉着圣子降生成人而进入人类历史之后,这两个时间基本上应被视为彼此相关:“时间”在“时机”内部结构更广泛的意义上川流不息,于是“时机”赋予“时间”更深刻的意义。任何表面上出现的事物都在充满天主恩宠的时机中产生更深远的意义。那么分辨这样的深远意义就等于解读时代的征兆。
这种检视“时间”(历史)的方式与任何探究“那真实发生的”(依Leopold von Ranke的说法)的历史实证论有别。当时代征兆出现在历史某一阶段时,那段历史就变成另一不同的记号。
先知的征兆
话语和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两种预言的形式。有时候那些言语和行动似乎在勾画一幅将天主拟人化的漫画。其实内中蕴含着比外在所看到的更多的内容。阿布拉罕·若苏厄·赫谢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精准地指出:“把先知神视所见的视为天主的形象或许比将天主的怜悯心肠当作祂似人的说法更为恰当”[3]。他进一步指出:“天主毫无条件地关切正义并非因为天主相似人。更好地说,人对正义的渴望乃是人相似天主的特征”[4]。怀有怜悯心肠的天主也透过先知的慈悲心肠与人沟通。
最好是把圣经中的预言当作先知个人对圣神在他心中活动的诠释,当作他在特定环境中内心所感受到的警示,而不是他对未来事件的精准预言。先知们之所以被接纳,大底因为他们对当前事态局势的见解,而非准确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为此,即使他们预言的事没发生,也不至于损及他们神秘经验的真实性。预言表面上的失败或天主许诺的没兑现也可以是时代的另一种征兆,这些征兆唤醒人们反省,进而忏悔皈依。
诠释的原则
权威的神学家们,包括解放神学的一些倡导者,提出诠释时代征兆的八个原则:
1)为能认出时代的征兆,首先需要让自己深深根植在信德上和他“那个时代”中。此外,也必须倾听他人的经验,尤其是历史受害者的经验。为能做到这点,非度友爱和关怀的生活不可。
2)一个本质上具有多层意义的历史征兆,它要表达的内容可能比特定环境中的某个人或某团体所能认知的更多。这一方面乃因为我们的存在和理解力有限,另一方面则由于不能把天主的启示缩限为实证科学[5]。
3)俗世认为:是人类在赋予他所感受的一切事物意义。然而,在宗教的世界观里面,造化的意义先人类而存在,它邀请人接纳它[6]。“在起初已有圣言”(若1:1):所有的存在其意义乃来自圣言并因圣言而存有。尘俗世界和宗教世界两者之间的表面冲突,可以经由以信仰来承认并诠释时代征兆一途予以克服。“已先存在的”和“在历史中产生的”这两种意义是任何健康的神学的两极。
4)识别并诠释时代征兆是纯属神学和灵修领域的任务。它远超单纯的社会分析。在这方面,它的重要前提是天主亲自临在人类历史中。正因为如此,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邀请我们在当代诸多事件中,在当今人们的诉求和渴望中,辨识天主临在和祂计划的标记。
5)欲了解时代的征兆需要辨识。除了基督降生为人这个事件之外,没有任何时代征兆,即便多么正面,能自视为完全是天主的恩宠临在于世界。罪恶与恩宠总同时存在于每个事件中。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不能把历史上的悲剧单纯地诠释为天主的惩罚。在希伯来基督信仰传统中,要解读时代的征兆非得从天主救赎工程的角度着手不可。
6)关于如何了解天主救赎的讯息一事,希伯来基督信仰传统无疑赋予了穷人和受压迫者优越的地位。在圣经中,不论是以色列人出离埃及这件基本事迹,或是先知们的出现,或是亚纳的颂谢诗,或者玛利亚的谢主曲,乃至基督使命的宣报,从未忽略指出穷人和受迫害者的痛苦乃是天主自我启示其救恩的首选之处。
7)在诠释时代征兆时,信仰、伦理和社会分析应三头并进[7]。缺乏信仰的透视,社会分析将失落事实内部最深刻的意义,仅停留在现象的外表观察而已。若缺乏社会分析及伦理责任,信仰将只流于虔敬的行为,其所能提出的也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答复而已。当我们视时代征兆为天主在人类历史中的临在并施展作为时,这些征兆也具有末世的意义。时代征兆乃为了历史的终结而出现的,因此应该被视为影响现在的未来,它继续不断地给此时此地带来新意[8]。
8)保禄六世教宗在他的《八十周年》(Octogesima Adveniens)宗座信函中托付给各国教友团体分析时代局势的责任,并根据福音来了解这个局势(参见手谕4号)。在这样的分析和了解过程中,时代征兆也可能以挑战当代人的信仰体系、他们的宗教生活、对圣经的诠释、神学的立场、生活的伦理规范等方式而呈现出来。比方说我们可以自问:“在奥斯威辛(Auschwitz)之后仍有神学存在吗?”。同样地,基督信徒在拉丁美洲迫害同一信仰的人这个事实被视为“审判的日子”:“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声称自己忠于同一个教会。他们都接受同一个圣洗,也一起参与同一个擘饼礼,吃喝基督同一的身体和血。当我们都坐在同一座圣堂时,堂外的教友警察和士兵却殴打、杀死教友儿童,或拷打教友囚犯至死,而其他的教友竟旁观着并有声无力地呼求和平。教会本身已经分裂了,审判它的日子已来到”[9]。
这类局势如果被视为对教会生活的挑战,就能激发人心和体制的反省与改变。
教会诠释时代的征兆
由于教会是天国有形可见的标记(参见《教会宪章》1号),所以诠释时代的征兆是教会的使命的一部分(参见《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号)。在这个诠释的进程中,“天主子民,…在天主圣神的领导下,…致力于研讨,在其与这时代人类共同的遭遇、需求及愿望中,何者是天主的计划,何者是天主亲在的真正信号”(《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1号)。
为此,教会应“以适合各时代的方式”,设法“解答人们永久的疑问,即现世及来生的意义,和今世与来生间的关系”(《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号)。一般而论,教会这个角色与它所负的先知使命一致。教会的先知性特征有两个层面:宣讲天国及与其相关的伦理,同时指正罪恶及偶像崇拜[10]。此外,教会作为时代征兆的诠释者,其基本任务就是做社会的良知,呼吁每个人和社会皈依。
教会的这个圣召始终给她招来反对和迫害。在提到这类处境时,圣奥斯卡·罗梅罗(Sant’Oscar Romero)说:“讲道比较容易…,可是当我们要将之付诸实行时,冲突就来了…。事实上每位愿意传播基督福音的司铎、会士或教友都将遭受迫害”(1978年7月16日讲道)。“在发生如此可怕的谋杀事件的国家里,如果那些受害者中没有司铎,那就很悲哀了。他们是实际生活在人民问题中的教会的见证”(1979年6月21日讲道)。
教会的本质乃天国的标记,因此当一个政府反对穷人时,教会必须协助政府修正并改变政策。与此同时,教会也不能忽略五旬节教派蔓延所展示出来的明显时代征兆,这类教派的某些团体甚至在最赤贫的人们中宣讲繁荣富庶的福音[11]。群体赤贫的状况要求人们、尤其是那些制造并使这种无人道状况继续存在的人发自内心的改变。从另一方面说,每个人的饥渴不仅仅限于食物、衣着和居所。关于饥饿,上主的命令是:“你们给他们吃的吧!”(玛14:16);关于口渴,上主的邀请是:“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若7:37)。教会必须诠释这些时代的征兆并给以具体的答复。
教会在履行其认知并诠释世界时代征兆的任务时,也不可忘记在自身的生活中解读这些征兆。教会是走向末世目标的旅途教会(参见格前13:9-10)。为此,它在旅途上所遇到的任何事物都处于发展与进步的进程中,而时代征兆则是“进程的标记”,是天主借以向在世旅途中的教会说话的途径。
降生成人的圣言是最终的标记
从基督宗教信仰的观点看,降生为人的圣言是宇宙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最终“标记”,因为祂是原始和终结(参见默1:8;21:6;22:13)。神学家卡尔·拉内(Karl Rahner)把原始基督宗教信仰启示的结束点从“传统”所认为的最后一位宗徒的去世退移到耶稣的死亡。为这位神学家来说,“启示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耶稣的圆满完成死亡而告终,也就是说,以十字架而结束,因为天主亲自在十字架上义无反顾、一劳永逸地将自己许给人类历史。除了祂的遗言之外,天主再也没有任何要说的”[12]。
依纳爵·艾拉古里亚(Ignacio Ellacuria)在他的征兆神学中,对“常在的征兆”和“其他的征兆”做了重要的区别。“其他的征兆”必须根据“常在的征兆”来辨认。为他来说,“常在的征兆”就是任何时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民,他们的“被钉在十字架”反映着上主仆人的被钉。洪·索弗利诺(Jon Sobrino)认为,被钉的人民乃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在历史中的真实临在[13]。整个人类历史都属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耶稣。祂把历史从“世俗的原理”(哥2:20)中解放出来[14]。为此,任何地方出现具体的解放事件,就可以被视为某个别的时代征兆,而此个别的征兆乃是“所有时代的最后征兆”的部分实现。
自然神学与历史神学
在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中,历史重新取得了它作为“神学园地”的重要地位。从基督降生成人的观点看,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固然充斥罪恶的扭曲,仍是天主施恩的时空场地。
历史是“天主启示的场所”,因此也是“神学的园地”,就如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书》第八章所提示的,超性的圣神就生活在历史中。是圣神的动能使受造之物叹息,渴望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得解放。同一的圣神使人的精神呻吟,希望从死亡中获得救赎;是圣神在我们内以“超越我们所能了解的方式”祈祷[15]。当然,是这位内在的圣神给以时代的征兆,在看似没有希望的局势中给人心燃起希望的意识。所有这些征兆可以诠释为圣神行动的标记,祂继续不断地引领受造物走向重生。而我们则受邀怀着责任感与圣神的动力合作。
由于历史是“神学的园地”,所以神学也应该是“公众神学”,具有完全融入生活的特征。之所以这么说,乃因为历史是整个人类共同的家,是属于公众的事。为此,一个“关心大众利益”、“有大众基因”、“公共实践”的公众神学,应该有能力解读和诠释时代的征兆。但由于大众事物本身没有一件在利益和看法上是一致的,所以公众神学在每个问题上经常遇到反对的意见。因此,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公众的兴趣只着眼在神学的研究本身,因为公众所关心的事总应该在与圣经的对话中确定。
时代征兆与宗教对话
下面我们要引述的文件突出了大公合一主义和宗教协谈在分辨时代征兆上的重要性,亦即需要发现天主“在当代人类共同的遭遇、需求及愿望中”(《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1号)的临在和计划。梵二大公会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以下简称《非基》)领会到“天主的照顾、慈善的实证以及救援的计划普及所有的人”(《非基》1号)的这份爱,并声明非基督宗教也反映着神圣真理之光(参见《非基》2号)。从大公合一主义的角度看,梵二大公会议的《大公主义》法令(以下简称《大公》)确认所有那些“在圣洗内因信仰而成义的人,即与基督结成一体”,“理应被视为主内的弟兄”(《大公》3号)。
当我们解读并了解各“时代征兆”时,可以发现它们与福音之间可以有某种程度的相辅相成作用。“时代征兆”以福音观点来解读,而福音若以与时代征兆对话的态度来阅读,则能重现其时代意义。福音作为天主向人类说的话,虽然以决定性的形式化身在基督宗教中,却未曾中断让其他宗教传统也看到圣言的标记(参见希1:1)。为此,一如我们引述的文献所显示的,对话的精神及其神学根基有助于参与宗教对话的各方按照自己的信仰传统,来解读时代的征兆。一个宗教传统的晦暗和模棱两可的地方可以在其他宗教传统的启发下变得明晰灿烂。或许可以展开一个对比的程序,在真正的对话中为不同的宗教传统带来净化的效果。这些宗教传统和哲学体系经常提供一些观念、隐喻和表征,非常有益于把圣经的讯息植入公众生活的环境中,让时代的征兆能以宗教协谈的立场来解读。
当前的一些时代征兆
根据前面所述,我们似可以分辨出一些时代的征兆。
那些以非暴力的方式反对不正义并矢志缔造和平的人民运动被视为时代的征兆,也是遵照福音的教导回应这些征兆的成果。的确,时代征兆能够是基督邀请我们追随祂实践今日使命的一个召唤[16]。
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征兆是被迫移民,这个现象要求每位善心人士伸出援手。从基督宗教信仰角度看,移民不但是需要他人行善的对象,他们也“在自己身上显示基督真实的临在…,耶稣的面孔已经在以奥妙的方式看着我们,尤其透过我们视为外人者的面孔注视着我们,有朝一日我们将在祂脸上读到祂对我们的判决书”[17]。确实如此,教宗方济各不论在劝勉人尽力协助移民上,或亲自为他们解决问题上,都视移民现象为当务之急。
当前任何其他棘手的问题,如2019新冠疫情、全球性的不正义、世界饥饿问题、杀害无辜生命、出生率下降、生态史无前例的严重快速恶化、原教旨主义、宗教激进狂热现象、暴戾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抬头及其引起的行动等等,都能够是时代的征兆,这些征兆邀请我们予以具体的回应。
回应时代的征兆
分析一个局势—“社会分析协调”—需要伴以解放神学家所称的“注释的协调”,在这样的协调中天主的话获得诠释,借以辨认出一个更能解放人的生活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实践的协调”,其目标在实行前面诸步骤所谈的结论[18]。
谈到此便出现一个重大的疑问:以信仰的眼光诠释某个时代征兆能在公众生活中产生什么影响?在圣经中,先知们诠释时代的征兆,并把他们辨识出来的结果通传给执政当局,而通传的方式有时是非常热切和急迫的。然而,未曾有过哪个执政当局完全听从先知们诠释的征兆。今天,在普世民主体系中,教会仍是公众的喉舌,它的声音有时被采纳,有时不被理睬,甚至遭强盛一时的政权讥讽。但教会不论遇到什么反应,它仍必须尽自己的职能,继续执行解读并诠释时代征兆的使命。
结语
当寰宇“最原始的征兆”基督使自身成为每次天主与人相遇的可能途径以及体验和诠释如此相遇的基本场所时,受造物和历史这两个“常在的征兆”便具体地敞开了空间和时间,在它们内我们可以检验“个别的征兆”。基督的门徒都受邀“在自己的灯盏内注满灯油,准备好灯芯,好随时点燃”以迎接新郎的来到,在“常在的”或“个别的”征兆中倾听上主的声音,看祂的神国在这些征兆中逐渐地拓展开来。
-
参见Benedetto XVI, Luce del mondo: il Papa, la Chiesa e i segni dei tempi. Milano, Mondadori, 2010, 93-101。 ↑
-
同上,245-253。 ↑
-
A. J. Heschel, The Prophets, New York – Evanston. Harper & Row. 1962, 260。 ↑
-
同上,271s。 ↑
-
参见A. B. IRVINE, 《Liberation Theology in Late Modernity: An Argument for a Symbolic Approach》,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78(2010)933。 ↑
-
参见D. J. NEVILLE, 《Christian Scripture and Public Theology: Ruminations on their Ambiguous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Theology 7(2013/1)17。 ↑
-
参见J. VERSTRAETEN, 《Towards Interpreting Signs of the Time, Conversation with the World and Inclusion of the Poor: Three Challenges for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ivi 5(2011)318。 ↑
-
参见M. J. MINELLA, 《Praxis and the Question of Revelation》, in IIiff Review 36(1979/3)18。 ↑
-
W. HUBER, 《The Barmen Declaration and the Kairos Docu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ession and Politics》, in Journal of Theology for Southern Africa 75(1991)55。 ↑
-
参见L. N. RIVERA-PAGÁN, «Completing the afflictions of Christ: Archibishop Oscar Arnulfo Romero», in Apuntes 28(2008/2)67。 ↑
-
参见F. NWAIGBO, 《Instrumentum Laboris: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 for the Second Synod for Africa》, in African Ecclesial Review, vol. 51/4 e 52/1, 2009-2010, 604。 ↑
-
K. RAHNER, «Morte di Gesù e conclusione della rivelazione», in ID., Dio e Rivelazione. Nuovi saggi VII, Roma, Paoline, 1981, 208。 ↑
-
参见J. SOBRINO, Jesus the Liberator: A Historical-Theological Reading of Jesus of Nazareth,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3, 255。 ↑
-
参见E. HUENEMANN, «Signs of the Times»: A Theological Reading. In Church & Society 75(1985)16。 ↑
-
J. MOLTMANN, «Sighs, Signs, and Significance: Natural Science and a Hermeneutics of Nature», in WesleyanTheological Journal 44(2009)20s。 ↑
-
参见L. JOHNSTON, «The “Signs of the Times” and their Readers in Wartime and in Peace», in Journal of Moral Theology 2 (2013)38s。 ↑
-
D. G. Groody, «Jesus and the undocumented Immigrant: A Spiritual Geography of a Crucified People», in Theological Studies 70(2009)316。 ↑
-
参见C. BOFF, Theology and Praxis: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