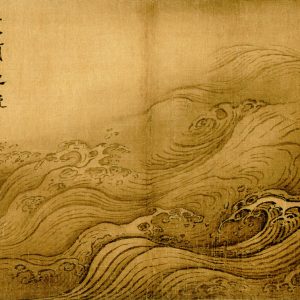在2015年5月27日的每周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方济各建议未婚情侣阅读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的小说《约婚夫妇》。教宗意识到,虽然曼佐尼既不是主教也不是神父,但像他一样的作家实际上可以在信仰和基督徒生活方面为教会带来许多启示。曼佐尼的这部经典作品描绘了伦佐和露琪娅充满艰难险阻的爱情故事。这部“关于婚约的杰作”中蕴含的教导至今仍对当代年轻人具有重要意义,它向我们展示的是:耶稣的追随者必须怀抱实现神圣正义的理想,勇于与苦难和巨大的邪恶势力展开英勇无畏的抗争。
在2016年关于家庭之爱的宗座劝谕《爱的喜乐》(Amoris laetitia,以下简称AL)中,教宗援引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参见AL 8)和其他现代作家(参见AL 107; 181)的作品。同样,这些作家从未被正式视为天主教徒和其他基督徒的教师,但他们却可以传授给我们许多重要的东西,包括这里所涉及的家庭生活。
此外,通过援引据说是教宗最喜好的一部影片《芭贝特的盛宴》,同一部宗座劝谕拓展了新的视野:“由于我们是为爱而受造的,我们知道分享美物是最大的喜乐”(AL 129)。芭贝特的无私分享为那些生活艰辛刻板的人带来了许多喜乐;她的爱向这些人展示了生活的纯朴情趣。
为了纪念但丁∙阿利吉耶里逝世700周年,教宗方济各于2021年3月25日发布了宗座牧函《永恒生命的光辉》(Candor lucis aeternae)。他在导言中指出,但丁“以诗歌之美表达了天主和爱的奥秘之深度”。稍后,我们将重新谈到这位佛罗伦萨诗人,以及他作为基督徒以至全人类的导师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可以补充说,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来便既是学徒也是教师,无论他们是否与但丁一样受过洗,也不管在教会或社会中身居何位。正如耶稣会神学家伯纳德∙朗尼根(Bernard Lonergan)在其经典著作Insight(《洞察》)中所观察到的,“话语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艺术,是每个人(向别人)揭示自己所知事物的媒介”[1]。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关于教友的教导作用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65)向所有能够为教会教育作用作出贡献的人传达了一种具有包容性以至普遍性的观点。所有的基督徒都因接受洗礼而与基督分享作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职务”。出于对教友接受这三重职务——特别是先知职务——的直觉力,圣若望∙亨利∙纽曼(San John Henry Newman)于1859年写下了他的重要文章《教友与教义探讨》[2]。
然而,纽曼并不是唯一为梵二会议承认男女教友的教育潜力而铺路的人。在《平信徒神学》[3]一书中,伊夫∙康加(Yves Congar)以三章的篇幅对教友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君王(按这个顺序)职务加以论述。此外,大公会议开幕前不久,一位将在梵二会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神学家杰拉德∙菲利普斯(Gérard Philips)撰写的另一本关于平信徒的书于1962年问世:Pour un christianisme adlte(《对于一个成熟的天主教来说》[4]。在该书的一个章节中,他阐述了平信徒作为“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种职能。
梵二会议明确引入了教友传教的观念,为教会大公会议开启了新的路线:详见《教会宪章》(题为Lumen Gentium,即《万民之光》,简称LG)第一章的第30-38号,以及《教友传教法令》(Apostolicam Actuositatem,简称AA)。此外,梵二会议其他文件中的一些条文也涉及到教友传教:例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简称AG)的第15号和第21号。此前举行的二十届大公会议从未提出任何关于教友的生活和使命的教义,更没有涉及他们作为先知的资格[5]。
《教会宪章》第四章阐述了教友作为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职务(以此顺序)。首先,“永远的最高司祭耶稣基督” “把自己司祭职务的一部分赐给教友们,要他们在圣神内献上灵性的崇拜,以光荣天主,并使人得救”(LG34)。
其次,“基督是大先知,祂[……]宣讲了天父的王国”,“并仍在尽祂的先知任务,[……]基督不仅借着教权制度,[……]而且也让教友们成为祂的见证[testes]” 以及“信德有力的宣扬者[validi praecones] ”(LG 35)。在此前的条文中,《教会宪章》宣布,教友的“家庭犹如一个小教会,父母应该以言以行做他们子女信仰的启蒙导师[praecones]”(LG 11)。同样,教宗方济各也经常强调父母作为导师的基本角色。例如,在结束2015年5月20日的公开接见活动时,教宗为所有的父母祈祷,祈愿他们能够以必要的信心、自由和勇气来履行这项身为导师的使命。
第三,“基督也渴望通过教友们开拓祂的王国”。关于教友的君王职务,《教会宪章》作出了比其司祭和先知职务更为详细的阐述(参见LG36)。
所有的受洗者“在基督的司祭、先知和君王的职务上成为分享者”,因此他们“在教会和世界上履行整个基督徒应有的使命”(LG 11)。他们受召进行训导(作为先知)、圣化(作为司祭)和治理的职务(作为牧人-君王)。
教友以何种地位参与训导
然而,由于教友并非“圣职人员”,《教会宪章》明确指出,他们与牧人不同,不具备“以基督的权威”进行“训导”的地位(参见LG32)。只有领受圣秩的神职人员才是“代表基督的人”(LG 37)。大公会议阐明了教友与晋牧主教及晋铎神职人员在基督的先知任务和训导任务中的不同地位:教友是参与者;而主教及与他合作的司祭神职人员,作为基督的合作者,是这些任务的执行者。
关于教友的先知和训导的角色,梵二会议承认,未经晋铎的教友是受基督任命而为祂的王国作福传工作的“活工具”(参见LG33)。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友们同样能够以基督的名义进行训导,利用祂的权威,代表祂的位格。正是藉着祂的安排,教友被邀参与“教会的救世使命”(LG33),特别是参与祂作为先知的训导任务。
《教会宪章》在第四章中提出了另外两个有用的概念:所有人的神恩(参见LG 30)和教友们的经验(参见LG 37)。这两个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不分割教会和教友训导任务的情况下对其加以区分的可靠方式。主教因晋牧而担负起导师的职务,教友则可以通过个人的神恩和经验成为教会和世界的有效导师,“加深对启示真理的认识”(LG 35)。
在梵二会议结束之际,《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简称GS)以独特的方式在教友训导中将教会与世界结合在一起:“普通信友在整个教会生活中既负有积极任务,故他们不独应以基督信徒精神薰陶世界,而且其特殊使命,便是在一切事上,尤其在社会生活,替基督作证”(GS 43)。这意味着平信徒不仅在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参见LG5;AA11;30),而且在公共活动,特别是在工作场所中行使他们作为基督见证人的先知职务(参见LG25)。
最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那些[……]”作出“大力贡献” 的 “[平信徒]男女教理讲授员”(AG 17)表示赞扬。也就是说,教理讲授员是导师,他们因此理应被列为教会训导的基本人物。
作家和导演
毋庸置疑,针对教友在教会中的任务以及为教会的服务,尤其是关于他们的教育使命,梵二会议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但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一教导职务的实践,并像教宗方济各一样,指出那些对教会有所传授的受洗信徒的榜样。实际上,他们是“生活中的传授”(《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ei Verbum[DV], 12),在天主自我启示的教育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启示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高峰。
让我们从作家和电影导演这两个群体谈起。对教会来说,他们是“生活中的传授”中的导师和重要声音,是天主自我通传的媒介之一。
“七罪宗”是由伊瓦格鲁斯(Evagrius Ponticus,345-399)和大额我略(Gregorio Magno,约540-604)发展而来的传统,它指的是骄傲、悭吝、迷色、嫉妒、贪饕、忿怒和懒惰。伊瓦格鲁斯和大额我略以这种方式重新阐释了关于人的罪的真理。当我们获得耶稣的喜讯时,我们应该认罪悔改(参见谷1:15)。
此后,晚于大额我略几个世纪的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以想象中一个漫长的攀登炼狱山的过程对伦理道德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把那座山分为七层,在那里,罪人被洗净七种罪宗。这些罪被依次排列,从最严重的骄傲到最不严重的迷色。虽然明知《圣经》中的十诫训导,但丁却认为七罪宗的教理更易于传播。
事实证明,诗人的这一选择非常成功。数百年以来,但丁的《炼狱》已成为一部生动的手册,使基督徒能够面对自己所犯的罪审视良心。这一教理得以传延至今,其中也有但丁的贡献。通过由九位导演执导的电影《七罪宗》(1962年)以及一系列类似影片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传统教理依然稳固有效。另外,可以说明这一点的还有马塞尔∙马索(Marcel Marceau,1923-2007),他将这些罪以戏剧化的形式通过哑剧呈现给了他的观众。
1993年的《天主教教理》列出了有助于滋生其他恶习的七罪宗(第1866号)并分别对其进行了阐述:骄傲(第1931号)、悭吝(第1849号)、迷色(第2541号)、嫉妒(第2553号)、贪饕(第2290号)、忿怒(第2302号)和懒惰(第2094号)。
通过想象1300年复活节之际对另一个世界的朝圣,但丁对基督教会起到的教导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一条关于罪的教理。《神曲》是一部来自天主的启示和人的聪颖的杰出产物,其中充满了数不胜数的教导,广及自然理性的作用、“天主经”祈祷天主和人类之爱以及许多其它真理的启示,甚至向我们展示了人生的目的和目标:对三位一体的天主的荣福直观。任何一部由平信徒撰写的作品都未曾达到但丁的水平,在基督宗教以及其他领域起到如此强大的教育作用。
鉴于其巨大影响,《神曲》不仅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不朽经典巨著,也堪称继《圣经》之后的一部“教会训导”基本著作。但丁留给我们的是最伟大的神学著述之一,应该说,它可以与两位神父的著作相提并论:一是很快便成为主教的圣奥斯定的《忏悔录》,一是神学大师,圣多玛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但丁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基督徒艺术家,其中包括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6],这证实了他应被视为在俗基督徒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然而,但丁并非独一无二,与他同样参与“训导教会”的还有许多其他男女作家,包括诗人多玛斯∙斯泰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和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护教者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克莱夫∙斯泰普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罗曼诺∙瓜尔迪尼(Romano Guardini)和多萝西∙赛耶斯(Dorothy L. Sayers);小说家乔治∙伯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ëdor Dostoevskij)、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O’Connor)和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j)。所有这些人士都堪称教会的导师,因为他们帮助无数男女理解和实践耶稣的信息。
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忘记诸如诺里奇的朱利安(Giuliana di Norwich)、宾根的赫德嘉(Ildegarda di Bingen)和锡耶纳的加大利纳(Caterina da Siena)等古典神秘主义者。赫德嘉、加大利纳、阿维拉的德兰(Teresa d’Ávila)和里修的德兰(Teresa di Lisieux)对祈祷和灵修生活其他方面的教导作出的贡献得到了正式认可,她们已被列为“教会的圣师”。这些圣女虽然从未领受过圣秩,但她们作为创意导师的地位不仅早就在基督教会中得到认可,并同时已超越了教会的范畴。
平信徒以电影为教导形式
在一个以屏幕艺术为主导艺术形式的世界里,影视作品不应该被忽视。一些影片直接采用圣经叙事,比如达伦∙阿罗诺夫斯基(Darren Aronofsky)的《诺亚》(2014年)、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基督的苦难》(2004年)、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玛窦福音》(1964年)和佛朗哥∙泽菲里里(Franco Zeffirelli)的《纳匝肋的耶稣》(1977年)等等;另一些影片则与圣经信息进行更为婉转的对话,例如丹尼斯∙阿坎德(Denys Arcand)的《蒙特利尔的耶稣》(1989)和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沉默》(2016)。
我们不能忽视描写基督徒生活的电影。泽维尔∙波伏瓦(Xavier Beauvois)执导的《人与神》(2010年)介绍了1996年阿尔及利亚内战期间被杀害的9名熙笃会隐修士的生死经历。埃米利奥∙埃斯特韦斯(Emilio Estévez)的《朝圣之路》(2010年)讲述了一位医生在其成年儿子不幸去世后踏上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并在那里遇到其他三位朝圣者的故事。这一类影片是基督徒教育使命的一部分,它们所展示的是基督宗教信仰在行动和敬拜中的表达。
优秀影片讲述人类救赎故事的作用并不亚于文学杰作,例如《午夜牛郎》(1969年)、《蓝色情挑》(1993年)、《红色情深》(1994年)、《老爷车》(2008年)和《三块广告牌》(2017年)。人们也许会问,是否可以将这些影片称为“预传福音”?无论答案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传达的是人被基督的宝血救赎的信息。
艺术家
一支由雕塑家、建筑师、圣像作家、画家和挂毯编织者组成的庞大平信徒队伍以事实证明,他们是有效的基督徒教师。其中的许多人以匿名的形式向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传授如何敬拜,信仰什么,如何活出信仰。
从基督宗教初期的地下墓穴开始,艺术家们便开始了对教会进行信仰的传授。当基督宗教艺术发展壮大之后,一些风格辉煌壮观的建筑纷纷涌现,比如罗马的圣母大殿、蒙雷阿莱修道院及主教座堂、沙特尔主教座堂等等。这些建筑及其内部装潢至今依然是滔滔不绝的见证,通过大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创造者,它们传达了基督的信息和基督徒生活的特征。沙特尔主教座堂的彩色玻璃窗讲述了整个救赎的故事,每个窗口都是《新约》与《旧约》的相互诠释。
同样,绘画、壁画和马赛克以不亚于彩绘玻璃窗的形式宣讲并阐明基督信仰的福音,并向其致敬。许多画家聚焦于耶稣受难的故事,特别是圣体圣事的制度。在对《玛窦福音》的诠释中,乌尔里希∙卢斯(Ulrich Luz)介绍了八种最后晚餐的艺术体现,从杜乔∙迪∙布奥宁塞纳(Duccio di Buoninsegna)、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古典作品到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于1909年绘制的一部表现主义作品[7]。艺术家们集中体现了圣体圣事制度及其庆祝仪式在不同时期中的形成。他们或是将耶稣即将到来的死亡描绘为一种祭献,或是着重体现最后晚餐作为共融的时刻。这些艺术家也许从未料想到可能成为基督徒和其他人的老师,但事实上,他们通过个人天资和努力而获得了履行这一角色的能力。
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绘画作品属于同样情况。对这些画像的默观是众多基督徒和其他人认识耶稣的苦难和圣死含义,无论是拉斐尔(Raffaello)的《耶稣受难》(1503年)、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的《伊森海姆祭坛画》(1516年),埃尔∙格列柯(El Greco)、鲁奥(Rouault)和伦勃朗(Rembrandt)的不同作品,还是众多令人震撼的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受难画像。
此外,我们还可以回顾卡拉瓦乔(Caravaggio)、埃尔∙格列柯(El Greco)、格吕内瓦尔德(Grünewald)、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和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对复活的耶稣的描绘和解读。以上画家与其他艺术家向教会传授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与复活的意义。
籍着个人绘画天资,许多堪称基督教会杰出导师的平信徒画家还进入了历史话题。犹太画家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便是其中一例。这位《白色十字架》的作者于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发生的 “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之后绘制了这幅作品。当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分子捣毁了7500家犹太商业和店铺以及近1000座犹太教堂,逮捕了近3万名犹太男性,杀害了至少91人。那次大屠杀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性毁灭。
在这幅夏加尔作品的构图中,一束长长的白光赋予受难美感,也为基督的面部注入了一种祈祷的平静感,覆盖耶稣身体下部的祈祷披肩为这种平静感添加了更为强烈的渲染。画面的两侧突显了犹太人的痛苦:被钉死的基督右侧是一个被烧掠的村庄,其下方是一群乘船逃亡的难民,左边是一个被烧毁的犹太教堂。十字架下面,几个人正在徒步奔逃,一座点燃的灯台与基督被钉死十字架的光束一起,照亮了逃亡的犹太人。对于那些与他们的犹太同胞耶稣一起受苦的人,这些细节是美和希望的象征。
夏加尔的《白色十字架》描绘了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这幅画将这些犹太人与福音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联系在了一起,使我们联想到耶稣提到的人物,并在他身上看到这些人物的体现:饥饿的人、口渴的人、作客的人、赤身露体的人、患病的人和坐监的人(参见玛25:31-46)。夏加尔的这幅画教导我们需要延长这个名单:“我是一个受迫害的犹太人,你给了我庇护”。将夏加尔这样一个未受洗的犹太人与“教会的训导”相联系,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然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耶稣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他不仅成为教会的永远领袖,也是与犹太民族鲜活联系的个人体现。犹太人的经历继续教导着基督徒。通过一位非凡的犹太画家——基督“肉身”的兄弟之一,基督徒可以认识到基督受难的意义。
作曲家们是教师
基督宗教赞美诗和歌曲的作曲家在传授基督宗教的敬拜、信仰和行为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表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平信徒,另外一些是主教和神父。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基督宗教都形成了以《圣经》为基础的丰富音乐传统。Akathist是一首东拜占庭最优美的赞美天主之母的圣歌,其作者据说是执事圣罗马诺∙梅洛德(san Romano il Melode,公元6世纪)或是一位君士坦丁堡的教父。米兰的圣安博(sant’Ambrogio da Milano,约340-397)不仅是西方礼仪圣歌之父,也是一位主教。
然而,许多创作赞美诗和圣歌的人并非主教。各地神学院继续教授的圣乐往往源于非官方教会人士。事实证明,这些作曲家是“训导教会”的主要成员。《痛苦圣母继抒咏》(Stabat Mater)是一首取材于《若望福音》19:25-27具悲剧性的中世纪赞美诗,相传由一位非司铎的修道人士所创作,它描述了圣母玛利亚在她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被广泛用于感恩祭和拜苦路的礼仪活动中。此外,巴赫、勃拉姆斯、德沃夏克、古诺、海顿、帕莱斯特里纳、舒伯特、威尔第、维瓦尔第和其他著名作曲家还为《圣母颂》(Ave Maria)和《圣母赞主曲》(Magnificat)和《痛苦圣母继抒咏》谱了曲。虽然并非所有的作曲家都曾为以上三个文本谱曲,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为其中的某一个文本谱写了不同版本的乐曲。例如,乔瓦尼∙达∙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 da Palestrina)为《圣母赞主曲》谱写了35首乐曲。在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可能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圣母赞主曲》大合唱。关于我们的主题,在以上提到的音乐家中,维瓦尔第是唯一的司铎,其他八位虽然都只是受洗的平信徒,他们却以他们的作品教导了基督的教会。
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伯德、海顿、莫扎特、帕莱斯特里纳和其他古典音乐家创作的弥撒曲使无数人能够欣赏感恩祭这一作为基督信仰核心的圣事奥义。他们与许多无名的弥撒曲作者一起成为全世界教会中具有影响力的教师。巴赫的《圣玛窦受难曲》和乔治∙弗里德里希∙韩德尔(Georg Friedrich Händel)的《弥赛亚》也属于这一范畴。此外,许多器乐家、歌唱家、合唱家、合唱团团长和指挥家赋予这些作品生命力,这些平信徒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所有教区教堂都接收音乐家和歌手的宝贵贡献,对于信友来说,流行的圣乐有时比神父的讲道更具影响力。
结语
本文的出发点是教宗方济各所列举的一些被认为对教会训导作出贡献的平信徒典范。教宗向我们提出这些人物是对梵二会议强调家长及教理讲授者的先知角色这一路线的沿承。一些具有传播者和导师丰沛恩宠的平信徒可以发挥他们的个人魅力,成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优秀导师。他们能够超越纯理念层面,通过想象力的发挥对涉及基督宗教信仰生活的主题进行阐述。
在教会内部,西方和东方的主教构成正式教廷并负责官方训导。与此同时,无论是作为家长和教理讲授者,还是作为作家、导演、艺术家和作曲家,无数的平信徒也都可以通过他们的教导为教会的教育使命做出贡献。他们同样在基督内向他人传授天主自我通传的真理。
- B. J. F. Lonergan,Insight: Uno studio del comprendere umano, Roma, Città Nuova, 2007, 387. ↑
- 参见J. H. Newman, s., Sulla consultazione dei fedeli in materia di dottrina, Brescia, Morcelliana, 1991. ↑
- 参见Y. Congar, Per una teologia del laicato, ivi, 1953. ↑
- 参见G. Philips, Pour un christianisme adulte, Tournai, Casterman, 1962. ↑
- 针对这个关于教友的教理,可参见O. Rush, The Vision of Vatican II: It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Academic, 2019, 269-308. ↑
- 但丁对基督教图像学的影响也存在于中世纪的手稿中,比如保存在威尼斯国家图书馆的Marciana手稿。 ↑
- 参见U. Luz, Vangelo di Matteo, 4 voll., Brescia, Paideia, 2006-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