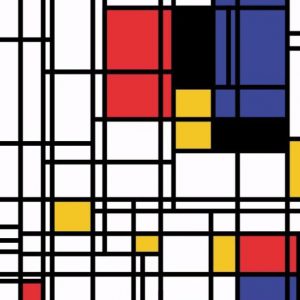“用完即弃”的平庸社会
社会学家们认为,我们已经营造出一个日趋平庸、虚渺和消遣型消费的社会并仍在继续这一进程。或许永远都是这样,但过去的人会竭力隐藏这种被视为消极的态度,而今天,平庸被肆无忌惮地接受。
这种平庸已经潜入社会生活体系并影响到它的许多方面。另外,它可能并不具有我们印象中所有那些低劣的特征,因为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平庸依然是人类存在的众多选择之一。事实上,西方新生代的公民平庸活动普遍增多。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只需观察一下他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总是过量,却缺乏实质性。他们通过易于接受的媒介处理这些大批量信息:通过音频或荧幕,通过几乎不需要脑力运作的极简信息,或通过社交网络。新生代摈弃了媒体,尤其是其中那些长篇幅的评论文章;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满足于浏览新闻标题而已。值得庆幸的是,尚有一些令人起敬的例外。
这种平庸集中体现于“用完即弃”,它在新型社会中甚为盛行。我们穿着用完即弃的服装,吃着用完即弃的食物——比如说大份即食快餐及最终被扔进垃圾桶的那部分剩饭——甚至还有用完即弃的生活伴侣:以往那种夫妻白头偕老的古老习俗让位于接连不断的婚姻系列,这种婚姻短暂得如同昙花一现,其中的承诺也已是所剩无几。
任何对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投以批判目光的人都会因这样一个事实而感到震惊:社交网络将生活组建为一连串近乎无关紧要的琐事,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无常:比如说,一种宜家观念,推而广之,将所有被这种思想潮流感染的人塑造成宜家一代。从家俱世界中摄取的图像可以描绘这一代人对眼前事物的热衷,既不需要预见未来,也没有对确定性的奢望。毫无疑问,促成这种态度的是当今工人阶级大部分就业和工资的临时性,这不允许为未来制定稳定、长期的计划;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这仍然不足以成为接受整个社会普遍沉浸于平庸的理由。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谈到平庸时,我们并不打算赋予这个词以负面的含义,而是想把它作为一种观察,当然,我们还对以下事实感到惊讶:人们的态度,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努力和扎实训练的传统价值正在让位于轻率和肤浅。
齐格蒙特· 鲍曼和文化的道德盲目性
当谈到“平庸”时,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参考。他是波兰人,于2017年1月9日在英国去世。使他成名的社会学理论是“流体的现代性”,这是一个变化和短暂性、放松管制和市场自由化的形象。鲍曼提出的流动性隐喻也试图表现个人主义和私有化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性,其特点是关系的短暂和不稳定以及不确定的道德原则。爱情变得起伏不定,对对方没有责任感,沦为虚拟现实提供的不露面的联系。“我们在一个流体社会的波涛上‘冲浪’,它甚至可以使宗教液化”。
评论家们指出,流体现代性是启蒙运动时期,人们为公民自由和放弃传统而奋斗过程中发现没有确定性的时代。现代人类当前面临着自由的义务,承担着这种自由所带来的生存恐惧和焦虑。面对这一事实,生存的直接解决方案是将自己淹没在平庸的海洋中。鲍曼笔下的阴郁景观也就如此出现了。
在他最近被翻译成意大利语的文章中,《道德盲目性》[1]尤为突出,在这篇文章中,这位社会学家再次重申了流体现代性可能导致的极端后果:道德指南针的丧失和伦理原则的缺失,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并恒久有效的契约,以及能够给西方社会大厦带来一些稳固性的行动。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经验能占据什么位置?如果宗教通常提供力量和安全,那么在流体的现代性时代,可以从它们那里期待什么?鲍曼是否开启了某种可能性?我们能否看到宗教回归的某些曙光–正如何塞· 玛丽亚· 马尔多内斯多年前指出的那样[2]–在这个渴望确定性的世界上?
鲍曼眼中的西方社会的悲观特征
鲍曼的去世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其思想的兴趣。在一篇文章中,心理学家Mónica Redondo提出了这位波兰社会学家的五个观点,作为解释我们当前世界的关键[3]。鲍曼的 “流体现代性 “切断了与过去固化架构连接的桥梁。近年来,由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生命哲学、价值观以及被认为是伦理和道德的东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流体现代性》一书中[4],鲍曼设法解释了现代的社会现象以及我们与过去几代人的区别。自2000年该书出版以来,这位波兰社会学家写了一系列作品,说明他对我们周围社会的看法:《流体之爱》(2003年)、《流体生活》(2005年)和《流体时代: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2007年)。以下是他的著作中看起来最重要的几点。
1)流动性现实在于打破固化的机构和结构。在过去,每个人的生活都按照特定的方式被建立起来,每个人都必须遵循既定的模式来决定自己的生活。鲍曼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成功摆脱了模式和结构,每个人都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模式,以适应自己的生活决定和风格。
2)根据鲍曼的观点,在流体生活中,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变成了一个不稳定和不固定的现实,其中没有固有的立足之地。与过去的固定结构相比,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可改变,都有一个保质期。在今天,鲍曼在《流体现代性》和随后的作品中所预料到的许多事情已经得到应验。他能够用爱、工作和教育的概念解读当今社会的运作,并能对新生代的人际关系给出定义。
3)在Tinder社交网络时代的流体爱情。祖父母的人际关系与我们所持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对承诺的恐惧、一夜情、爱情的失望等等: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所有这些可能只是家常便饭。对鲍曼来说,正是这些关系给他的 “流体之爱 “概念正名。在他看来,害怕承担责任和不得不放弃自由之类的东西,才是放弃依恋于某人的主要原因。流体生命是一连串的新开始,期限有限,没有痛苦。爱的关系最终变成了短暂的插曲,主要集中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当一个伴侣不再“有利可图”时,人们就将其搁置起来,寻找另一个。这不多不少正是Tinder应用程序的哲学。诚然,从那个约会搜索应用中也涌现出了永恒的爱情故事,但大多数用户在屏幕上滚动浏览一排排的面孔,直到找到中意的人共度良宵。
4)世界公民。如果有什么是我们不想要的,那就是人际束缚,这不仅适用于爱情,也适用于生活方式。在现代,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年轻人为了打破藩篱并结识与出生地不同的世面而到拉丁美洲或东南亚进行几个月的旅行。鲍曼的“流体现实”正描述了这种情况,它鼓励变动和寻找新的经验,但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扎下根来。尽管是世界公民,但同时又居无定所。
5) 铁饭碗不再吃香!在“流体社会”中,这种寻求新体验并使自己成为世界公民的理念也反映在工作环境中。我们的祖父母和父母一毕业就开始在一家公司工作,40年后又在同一个地方退休。然而,鲍曼解释说,今天的人们,无论是在爱情还是在工作中,都不想要人际束缚。所谓的“铁饭碗”已不复存在。工作是多变的,今天的市场要求公司内部不断变通。另一方面,鲍曼在他的作品中强调,工人也需要改变,他们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具备多面性和在不同部门工作的能力。
汉娜· 阿伦特,恶之平庸
但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一个“伦理平庸”的方面,鲍曼也提到过,犹太哲学家汉娜· 阿伦特已经找到了充分的解释。事实上,她提出了“恶之平庸”的理论。阿伦特1906年生于德国,1975年死于纽约,“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在哲学方面)。作为1933年纳粹反犹太主义的受害者,从1937年到1951年,她的部分时间是作为一个无国籍人度过的,当时德国政府剥夺了她的国籍(美国后来提供给她)”[5]。
虽然她是作为政治哲学家被研究的,但阿伦特不喜欢在哲学思考的背景下被归类。她喜欢称自己为 “政治理论家”,但《Vita activa》[6]等作品和她对其他思想家的不断批评证明了她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她最著名的作品是《恶之平庸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负责组织和分配集中营的后勤人员阿道夫· 艾希曼逃往阿根廷,以逃避战争法庭的审判。1961年,他无视国际法,被绑架并被带到耶路撒冷受审。那时,《纽约客》杂志请阿伦特记录下这次审判。根据这一要求,她写了《恶之平庸》,其中她不仅详细描述了审判的过程,还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尽管艾希曼促成并助长了那些毫无疑问的恐怖事件,但为什么他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一个邪恶的人?
这位女哲学家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从不否认,但他不认为他的行为有什么本质上的坏处。这位德国法西斯党魁声称,“我执行的是国家的命令”,此外,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 “好公民” ,执行他被委托的任务。从这里,阿伦特定义了“恶之平庸”。首先,这种平庸,正是因为它的平庸,没有促使她反思邪恶是“可怕的”这一事实,而是纠结于艾希曼为什么会允许或助长它。
对阿伦特来说,被告没有将其行为建立在强烈的意识形态或道德信念之上这甚至比行为本身更可怕。为什么一个正常的人,不作恶,除了执行命令外甚至没有任何架子的人,会被卷入那场巨大的暴行中?出于判断力的无能。阿伦特区分了知识和思想:前者是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是对所学知识的概念化,而后者则被定义为一种持续的内部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每个人在亲密的孤独中判断自己的行为。艾希曼没有“思想”,或者至少在他策划对数千名犹太人进行分类并将其处决时没有行使它。这使他成为一个 “新的邪恶代理人”,他丝毫不像那些受强烈意识形态信念驱使的人,而是加入了一个去意识形态化和无意识的群体,主动或被动地促成了“恐怖”。
关于判断力的无能,阿伦特区分了三个群体:1)虚无主义者,他们认为没有绝对的价值,将自己置于权力领域;2)教条主义者,他们坚持既定的立场;3)正常公民,类似于何塞· 奥尔特加· 伊· 加塞特所划分的人群,即,不加批判地接受社会习俗的多数群体。所有这些群体都没有阿伦特所理解的思想。她认为,纳粹主义得到了这三个群体的培育和鼓励,正是这一点让该国大多数人犯下了那些反人类的罪行。然而,这位犹太哲学家解释说,这种没有对话的情况本身并不是一种邪恶,更不会带来任何蓄意的坏行为。正是在极端情况下–如纳粹主义在德国的统治,甚至在其出现之前–邪恶的平庸作为同谋,甚至是对“恐怖之人”的同情。
阿伦特是马丁· 海德格尔和卡尔· 雅斯贝尔斯的弟子,他的思想可以与现代存在主义相提并论。在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Vita activa》中,这位哲学家对她所处时代的人类状况进行了研究。她将 “人类状况 “定义为决定它的因素,否认“人性”是第一参考。她强调了这一条件所依赖的“三项基本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所有这三者都被归入“积极生活”的概念中,每一种都对应着一种条件:生物性、世俗性和多元性。
必须恢复对生命意义的反思能力
与平庸打过交道的知识分子,如鲍曼和阿伦特,以及曼努埃尔· 弗莱约的一本书,Semblanzas de grandes pensadores[8],邀请我们阅读并促进批判性思维,为重新思考我们在流体文化和平庸背景下的生活。一个有“扁平脑电图”危险的社会,只想着玩乐、逃避现实、消费、“用完即弃”,绝对需要一种解药,正如Fraijó所言。
在漫长的、艰苦的、有时是无结果的反思之路上,我们并不孤单,在我们之前有许多男男女女(不过,后者在哲学教科书中出现得很少)。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前行的道路是一条被前人勤劳耕耘过的道路。1676年2月15日,艾萨克· 牛顿写信给物理学家罗伯特· 胡克:”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爬上了巨人的肩膀”。这个表达实际上似乎可以追溯到沙特尔的伯纳德(约1130年去世)。不管它的作者是谁,都值得我们关注。科学的社会历史表明,理性思维的发展通常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的工作。托马斯· 库恩(Thomas S. Kuhn)已经强调了科学共同体对于构建一个致力于加强、转变和推翻科学理论范式的重要性。同样,社会科学也是从对世界和现实的某些概念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从历史上看,正是所谓的 “思想家” ,即那些站在以前的思想家肩膀上的前卫思想,推动了对社会进程的解释。
我们必须重新学习思考,重视那些我们认为的“思想家”。需要兴起一代对现实有批判能力的男女,并决心不生活在转瞬即逝的平庸中。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构建跨学科思考的空间和平台变得迫在眉睫,并将占主导地位的大众文化从乏味中解放出来,这种文化只寻求消费,而不屑于改变生活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一项令人兴奋的任务。而与那些可以被称为’伟大的思想家’的人共同反思,为成为21世纪的信徒的可能性开辟了视野。
要划定“伟大的思想家”的概念并不容易。本书中我们提到的这个概念特别归于那些从理性(哲学)思考出发之人,他们阐述了不同的世界观、人的地位以及在全球化世界背景下人类价值和生活的意义。Fraijó特别提到了22位伟大的思想大师,从孔子到卡尔· 拉纳,其中回顾了马丁· 路德、伏尔泰、费尔巴哈、尼采和康德等不同的人物。
在我们这样一个逃避现实和平庸的文化似乎正在获胜的世界里,认识到曾经存在过并且存在着一批将反省当作核心关切之人,这可以作为一种解毒剂,有利于建设一个男女自由的社会,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结语
今天,有可能激发批判性的、理性的、非平庸的、跨学科的思考的可能性成为一种刚需,它将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神学家、经济学家和精神科学的研究人员(正如威廉· 狄尔泰假设的那样)聚集在一起,并一道致力于寻求和共同建立赋予全球意义的现实解释系统,并回答伊曼纽尔· 康德已经自省过的伟大问题:人是什么?
Fraijó在他的书的序言中说:“本书中提到的所有思想家都同意不屑于明显的东西,并致力于思考。从一开始,哲学就从这样的假设出发:没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蕴藏着美妙和不解。阿瑟· 叔本华很清楚这一点,他写道:”生命是痛苦的;我决定用反思度过一生”。20世纪最重视哲学思考的哲学家之一胡塞尔也给我们留下了类似的东西:“我必然要进行哲学思考,否则我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生活”。我们只希望费希特的话不是真的:“如果你开始哲思,就不会活着;如果你活着,就不会哲思。在我看来,将永远有可能把生活和哲学、思想和经验结合起来”[9]。
弗拉伊霍向我们提供的思想家的多面性观点,以及与其并肩工作的许多其他男男女女,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致力于对人类重大问题的多学科答案的认真研究,这始终是必要的。
- 参见 Z. Bauman – L. Donskis, Cecità morale. La perdita di sensibilità nella modernità liquida, Roma – Bari, Laterza, 2019. ↑
- 参见J.M.Mardones, Síntomas de un retorno.La religión en el pensamiento actual, Santander, Sal Terrae, 1999. ↑
- 参见M. Redondo,”5 ideas de Zygmunt Bauman que retratan a la sociedad moderna”, in Hypertextual (hipertextual.com/2017/01/5-ideas-bauman), 10 January 2017. ↑
- 参照 Z. Bauman, Modernità liquida, Roma – Bari, Laterza, 2002. ↑
- L. H. Rodríguez, “Hannah Arendt, sobre la banalidad del mal”, in Newtral (www.newtral.es/hannah-arendt-sobre-la-banalidad-del-mal/20191014/), 14 October 2019. ↑
- 参见 H. Arendt, Vita activa. La condizione umana, Firenze – Milano, Giunti – Bompiani, 2017 (or. 1958). ↑
- 参见同上,La banalità del male. Eichmann a Gerusalemme, Milano, Feltrinelli, 2019 (or. 1963). ↑
- 参阅M.Fraijó, Semblanzas de grandes pensadores, Madrid, Trotta, 2020, 353-370.作者是马德里国立远程教育大学的宗教哲学荣誉教授。 ↑
- Ivi,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