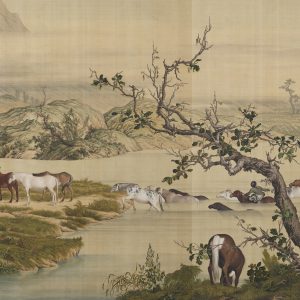心理创伤是个直到近日鲜少在研究领域受到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心理创伤不像肉体物理创伤那么容易予以准确的界定或验证核实它。最近几年发生的那些轰动的事件(例如从战场前线归来的军人的创伤或恐怖暴力袭击)都引发人们益加关心创伤的议题,将之列为许多子类别(sottocategorie),这大大弥补了过去的忽略。
创伤是什么?
从语源学看,创伤一字来自希腊文τραῦμα,即受伤(ferita)的意思,它明显指出这个名词的意义:创伤者乃指一个存在物所受的创伤印记,这个伤记有时是无法抹灭的。创伤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繋于发生的事件本身,另一个则是事件带来的后果。创伤的这两个层面,即客观如实的创伤(trauma oggettivo)及心理的创伤(trauma psicologico),两者互有关联,彼此可以包括或互为因果。若谁在年幼时他的情感和心理忽视,成年后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容易遭到侵犯。心理创伤可以定义为创伤后(post-traumatiche)经验的状况,是由不同性质的关系或紧张压力的事件所引起的,致使个人无法掌控处理,对他的生活和精神健康造成重大的冲击[1]。这种受苦状况引发的作用会以侵入性和持久性的形式呈现出来,它要比身体恢复健康所需要的时间更长。
事实上,这里所提及的种种经验乃是由现时前后不同时刻发生的事件因素共同汇聚而成的,这些因素在人身上造成了重大的改变,限制了人领会存在之美及令他喜悦之事的自主和能力。当人遇到令他震惊的事件时,身心都会受到强烈的反应所撞击,这样的剧烈反应形成一股激动和感觉上的混乱旋风,直至超越了人承受和忍受的能力。在缺乏情感的支持下,事件持续的时间和其重复,足以导致强烈的情绪和生理状态的冲击:这样的情绪和生理状态又会引发神经系统机能不良,扰乱思想、感觉和行动的方式。被困在如此创伤中的人容易受到种种的刺激而引发强烈反应,让人觉得他是个经常处在危险中的人。
皮埃尔·加内(Pierre Janet,1859-1947)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先驱。他认为心理创伤乃是人的智能没有能力为发生的事件找到一种意义,没有能力给该事件整理出一个概要,无法予以整合,致使当事人心神破碎,终至引发“多重人格的困扰”,即自我内在的破裂,也就是今日所称的“分裂人格障碍”。在认知层面上没有能力回忆创伤的事件,使得该事件经由记起、甚至强行记起创伤经验的刺激(如噩梦、幻觉重现、味道的存在、声音、衣服的特别式样)而重新发作,却不会意识到这一切都与过去的事件有关[2]。
创伤主体的面貌
面对同一个灾难事件,为什么有些人会受到创伤,另一些人则不会?看来灾难造成的不同撞击似乎在于多种因素:危险的严重性和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灾害的强度;如果灾难事件既接近又突然,则令人无法及时应对。要是事件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则创伤事件会是极具伤害性,而且所产生的影响也将更有害和持久。
此外,重要的是必须确知当事人是否重复处在这种威胁性的状况中,而且在事发时他有多大年岁:当类似的状况越多,而年岁也越小,则身心脆弱者的心理运作越是容易遭到侵蚀而患上这个病症。从事某种职业者,例如军人、维安人员、医院急救人员、紧急介入人员如消防队员和宪兵等,也比较容易暴露在遭受创伤的危险中。
创伤足以导致人一时的错乱;然而,当一个人越能掌控自己的情绪并拥有健康的自尊,他越能面对并克服创伤的经验。当事人以往的经历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最后评估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个人在童年时缺乏关爱,受到忽略或遭到侵犯,他日后遭受的创伤事件更具破坏力,一如黑洞吸食他所有成熟的可能性[3]。
一个人能以什么强度去面对创伤的事件也有赖他的人格结构以及他神经或大脑遗传上的基本精神病学状态。在人格结构方面,它的特征尤其可以追溯到学者所称的“五大(Big Five)”,即“人格的五个特征(cinque tratti della personalità)”,这些特征影响人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1)向经验开放:倾向于从事活动,培养兴趣,丰富个人的内在世界,避免自我封闭; 2)外向性格:具从内向外看的能力,对被要求的事物基本上怀抱信心,以热忱和兴奋待之;3)认真仔细:渴望以慷慨和专注的精神认真细心从事被托付的工作或委以的责任;4)称心愉快或友好:乐于贡献自己帮助他人,对他人表示关心,甚至舍己为人;5)感情稳定:这与内在平衡、性格类别以及它面对局势和意外时可能发生的变化、乃至应对侵犯等等有关[4]。
每个人的人格都由这些不同的独特特征交织而成。这些特征如果彼此交互作用良好,则有助于在心理上形成面对并克服创伤压力、不被其压倒的能力(resilienza);形成不以受害者或遭破坏的心境来看创伤的侵害性,而是预置防犯并超越创伤与遭侵犯的能力(proattivo)。心理学家苏桑内·柯巴萨(Suzanne Kobasa)指出面对并克服创伤压力能力(resilienza)的三个特征:1)殷勤(l’impegno),即热心参与其事的(coinvolgersi)能力,知道自己为某人可能是重要的;2)控制(controllo),即亲自掌握事况,深信自己始终具有可运用的权力;3)接受挑战的乐趣(gusto per la sfida),它使人视创伤的事件为可能的契机(比如帮助陷于困境的人),而非一种威胁。这三个与个人意识相关的特征都可以经由利他主义的精神培养出来,这一点容后述[5]。
另一个能够有助于建立面对并克服创伤事件的能力(resilienza)的重要因素就是拥有重要的情感关系(relazione affettive significative)。一个情感稳定、带有敬重心和同理心(empatia)的生活环境能有助于展现个人的天赋与能力,这为面对创伤事件极其重要。精神分析家布鲁诺·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遭轰炸创伤事件对儿童造成情绪冲击的研究指出:如果双亲被忧郁所击倒,则子女同样陷于恐怖;反之,要是双亲带给安全感,则子女会获得消除危险感的奇异效果。双亲的临近,他们使子女放心的声音都足以安抚孩子们的心情,使他们不再有任何恐惧:“双亲面对事件的态度会完全改变子女的心境,因为子女根据双亲处世的经验来建立自己对世界的解读”[6]。
例子指出面对并克服创伤事件的能力与儿童对其所依赖的重要形象的依附程度(grado di attaccamento)有关,这些形象传递给儿童面对困境的信心,使他们能够进行 “思想综合(sintesi mentale)” (皮埃尔·加内喜爱的名词),掌握事态。
根据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的看法,“依附是人从生到死整个人性态度的一部分”[7],它和幼年时与母亲建立的深刻与稳定的关系有关。这个关系代表着其与双亲维系在一起的无形的情感纽带,并赋予安全感、保护和面对困境的能力。依附需求对儿童的成长是必要的,这在每个人的情感、社交和认知发展上占有关键地位。儿童知道可以依靠父母稳定的爱和信任,这正是他安全可靠的依附,这样的依附有助于儿童培养自尊(autostima)的能力,这样的能力使他在未来能建立稳定的关系,有力量以预先防范的能力(proattivo)来应对紧张艰困的局势。如果儿童没有可靠的依附,他即使是渴望,也将倾向于避开关系,以免陷于对自己缺乏自尊的失望;或将倾向于表现过度的依赖,以反常和令人窒息的方式依附于人,在焦虑和不稳定的性情中过着隔离和冷漠的生活。
因此,创伤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解读创伤、他所依据的价值观、尤其他是否处于孤单或身边是否有人能够帮助而定。有可靠的依附、使人觉得是团体中一份子的家庭气氛,乃是主要的保护形式之一:“那些意义健全的体制系统很能够处理灾难和暴力冲突”[8]。这是一个基本的区别因素,在遭受战争和大动乱地区所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对遭到侵犯的人来说,如果他有可信赖的人在旁,可以与之倾诉,觉得自己受到重视,这为他面对悲剧创伤的后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反之也是一样:例如离婚事件,依据当事人与其双亲及家庭气氛所建立的关系,它多少是个创伤;要是离婚事件出于夫妻关系紧张、争吵、乃至暴力冲突,则两人的分离或许不至于给幼小子女造成过度的震撼,如果离婚是未曾预料到的,则将产生我们前面提到的意外后果。
“有害于童年经验的研究”(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Study)
创伤的后果曾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主题。1995至1998年在美国进行的“童年有害经验的研究”(ACE, 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Study)曾涉及17000位成年人。该研究特别指出某些创伤的经验,这些经验尤其发生在从出生到十七岁的年龄之间。当事人特别遭到“暴力、性侵和忽视;目睹家庭或团体的暴力事件;有家庭某成员试图或死于自尽;家庭与妄用毒品问题有关;有精神健康的问题;因双亲离异而造成的内外在的不稳定;因家庭成员坐监而造成家庭不稳定状况;居食不足;歧视与傲慢欺人”[9]。
这项研究指出,接受研究的成年人在儿童时期遭受的不良经验与他们之后的成长过程有重要的关连:64%的受访者承认在十八岁之前曾遭到至少一种类型的创伤事件;17.3%的受访者,即六人中便有一人,承认经历过至少四种创伤事件。
对照成年人,又可以发现遭受创伤和引发下列各种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如吸烟、酗酒与吸毒,暴力行为,犯罪,凶杀,人际关系障碍,情绪容易失控,性关系混乱,抑郁症,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病,精神障碍,自杀(最后的几个状况占受访者的50%)。此外也发现遭受这类创伤的人有困难接受良好的教育,也因此不易谋得良好的职业。从健康的角度看,有害于童年的经验(ACE)也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加拿大和美国每年必须为此付出约7500亿美元的经费[10]。
这项研究给探索和推广有助于降低创伤对患者影响的个人及社会因素提供一些提示。该研究证实:拥有安全可靠的依附具有绝对重要性,它乃是预防受创伤最好的方式。最后,这项研究也指出上述那些问题极有可能遗传给后代:“这意味着儿童时期承受的有害事件越多(事件发生时的年纪越小),则出现在成年期的病症也越多,包含那些与影响健康有关的行为举止”[11]。
这些研究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有效提供幼年期遭受创伤冲击的最准确资讯,同时营造有利于儿童的环境,加以保护,以预防在成年期引发的严重和慢性疾病。根据这些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将有害于童年的经验(ACE)列为必须避免的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的危险。该机构同时提到在治疗层面上可行的干预措施以及在教育、法律和保健方面的建议,藉以控制有害的局势并增加生活的才能(life skills)[12]:1)通过培训帮助并支持双亲和保健人员推行教导性而非暴力性的父母职责;2)加强学校的素质教育,推行相关活动,加强个人面对并超越创伤事件或困难时期的能力,指明暴力行为的危险;3)展开预防侵犯及个人保护的计划,学习如何寻求帮助;4)在学校中增进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的同理心,加强合作的环境,关心弱者,阻止暴力;5)增进认识极不受重视的父亲教育职责;6)颁布禁止暴力惩罚的法律;7)设立服务机构,为暴力和性侵受害者提供诊断与协助[13]。
治愈创伤?
人真能够从创伤中获得治愈吗?重要的是远离奇幻般的期待 :“治愈”不意味着让与创伤事件相关的记忆或情绪消失于无形;而是使记忆和刺激取得任何另一种思维的能力。就如身体创伤治愈后伤痕仍然存在一样,接受一个业已过去但事迹仍将存留的事件。
心理治疗对创伤能够提供重大的帮助,特别因为这样的治疗可以使发生的事件转换成言语,使或许是第一次发生在当事人身上的事件处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中;而当事人对事件的口头记录可以让事件在一定距离内得到体现(因为言语既是抽象的,所以需要与事实保持距离),同时整合情绪与认知。这就是卡莲·布里森(Karen Blixen)所说的真理:“所有的痛苦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让它们进入一件故事中,成为可以叙述的历史”。
在治疗的时候,重要的是首先该正视对发生之事的判断问题,创伤越是重大,则判断会越尖锐和片面。不幸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的事态会颠倒过来:受害者不同于创伤肇事者,反而会感到内疚。事实上,罪过既然有其责任,所以认罪乃是行使掌控事态和表示对发生的事件拥有权力的一种方式 ; 这是逃脱混乱、对不可抗拒的力量感到无能为力的猎物的心态;是拼命设法逃避精神失衡的企图,即使这个企图是错误,而且具破坏的形式,亦在所不惜。事实上,罪恶感足以严重阻碍疗愈的进程。
在治疗上有多种以防范的方式面对创伤的建议[14]。其中之一就是练习(Mindfulness),它旨在刻意增加个人的意识,以便了解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以不同品质的方式生活并与外界互动。“活在当下(presenti al presente)”,有意识地活在此时此地,接纳记忆和思想,但不予以判断,也不与之对话。这就是练习所建议的做法:“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和注意的焦点时,我们可能就在使用大脑的种种回路,它们首先建立意向的图表,并调整我们对他人的注意力”[15]。
另两个进一步的治疗建议也与有关。第一个建议是感觉运动心理疗法(PSM, Psicoterapia Sensomotoria ),它聚焦在人身上卷入创伤的那些部分,指出与创伤有关的情绪和思想。该疗法的目的在使患者得以掌控这些感觉,并因此减轻感官运动上的创伤效应,重获基本的安宁[16]。
第二个建议是心智化治疗(MBT,Trattamento Basato sulla Mentalizzazione )。这项疗法旨在承认创伤在心智运作上造成的伤害,它涉及情绪-肉体(emotivo-corporeo)和主体间(intersoggettivo)等因素。在治疗上,患者受鼓励“了解创伤造成的情绪性质;点明与创伤相关的情绪;回想与过去和当下生活相关的情感;集中注意力于出现在后创伤期症状中的不明感觉(如羞耻,屈辱,无助感,亦即无力感及无效感);探明这些情感是否存在于过去生活上的特定状况中,而且是否始终被他人所了解”[17]。这第二个建议旨在有利于心理状态,使患者能因此开始展开正面和稳定的活动及人际关系。这为重塑患者的真相及其各方面完整的自我很是重要。
最后我们还得提到经由眼睛活动进行脱敏作用和重新处理的治疗法(EMDR, Desensibilizzazione e rielaborazione attraverso i movimenti oculari)。这项治疗所依据的前提是任何不适或病态都源自某个先前的事故:“上述EMDR这项疗法的目的在使过去功能障碍的残余快速进行新陈代谢的作用,使之变为有些用途。基本而论,藉着EMDR疗法,功能障碍的数据在形式和意义上将受到自发性的改变,有利于患者的洞察力和情绪得到提升,而非自我贬低”[18]。治疗工作的步骤集中在创伤事件,开始时闭眼进行重新整理该事件,专注在导致干扰的事物上,并重复如此做,直到在治疗医师指引的活动下,有能力张眼走完重新整理的全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操作练习在使患者逐渐改变内在对创伤事件的感受之后,将减轻他受创的症状[19]。
当创伤成为机遇时
内心面对创伤和困境的能力(resilienza)的特征之一,一如所看到的,就是关心他人的世界。这是走向创伤疗愈重要的一步:乐意帮助他人走出创伤的隧道乃是使自己不再受困于不适(disagio)及知道发现自己生命对他人是重要的一种标记。这是一种看来矛盾的帮助:患者本身活在承受创伤的另一种方式中,却不再困于自己的创伤,他忘了自己的处境,无偿地去帮助他人。精神病学家埃尔文·亚龙姆(Irvin Yalom)指出,当一位创伤患者不再只关心自身和自己的问题,而是设法去帮助他人时,这项关心他人的疗法最具效用:“据说克林顿·杜菲(Clinton T. Duffy,圣奎亭监狱的传奇人物)曾肯定指出,帮助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帮助你。人需要觉得不可或缺”[20]。
个人的困难并不因这项疗法而被遗忘,但感觉自己有用却能够提供另一种空间,使人得以怀着更具目标的态度而非受害者的情结来面对生命,让自己体验到先前未曾感受过的与他人的和谐之美。甚至,正由于自己受到创伤,所以更有能力帮助他人,因为他知道帮助创伤者意味着什么。这是疗愈自己同样重要的一面:在帮助他人的时候,发现这正在帮助自己。
例如,发生在史特凡尼亚(Stefania)身上的事就是这样,她失去了十六岁自尽的儿子路易吉(Luigi)。她因内疚而倍感痛楚,这是苦中之苦。起初她自问什么地方做错了,因为她未曾发现路易吉正处于生活找不到答复的困境中。她的创伤因旁人在背后的无情闲言而益加严重。于是这位母亲寻求帮助:她不想听安慰的话,只愿意有人知道聆听她的倾诉而不加予判断。她终于找到一位和她遭遇相同悲剧的母亲。从她们两人的会晤聚谈中萌生了创立一个协会的构想,以帮助有同样遭遇的人士:这个协会透过小组、会议、研讨会以及经验分享,提供处理哀悼的可能性。史特凡尼亚因为慢慢地关心他人的痛苦而学会了找到内心的平安。
儿子的去世为史特凡尼亚仍然是个谜,但她发现当自己不再自责或寻找儿子自尽的原因时,她的感觉便良好。她的生活更着重当前,更加关心其余的子女,而这些子女也继续感到需要她:“在极度痛苦中,积极的一面就是为他人的需要贡献一己之力。今天,当我述说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时,我的心很宁静,因为我的痛苦已经变成回忆与路易吉度过的美好时光和那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爱”[21]。
许多有意义的经验指出痛苦和愤怒能够变成为帮助他人和预防创伤的动机。吉诺·切格汀(Gino Cecchettin)是最近几个月新闻频繁报导的悲哀无稽死亡的茱莉亚(Giulia)的父亲,他决定创立一个基金会,“为永远纪念他的女儿并传布爱和希望的讯息”,同时致力推动学校中的情感教育,以增进对话和预防暴力,并为可能结束的情感关系举哀(l’elaborazione del lutto)。吉诺·切格汀认为他这项创举是“一项鼓励参与的路程,它将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牵动在这段时期关切这项创举并支持我们的使命的政府机关、组织和社会人士,以便保证各方的参与、创举的多元性和交互作用。广泛的参与将是这项创举获得更大和持久影响力的保证”[22]。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创举是尼科·阿甘波拉(Nico Acampora)发起的:他发现儿子患自闭症(autismo),于是决定开一家披萨店(pizzeria),邀请患自闭症的儿童参与共同的计划,让他们找到工作,获得重视,实现自我。随着时日的推移,他的讯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自闭症披萨店的伙伴们获得参议院、众议院、欧洲议会、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的接见,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更于2023年世界关心自闭症日当天,特地前往蒙札(Monza)的自闭症披萨店访问。尼科·阿甘波拉这项创举更自告奋勇作为代言人,呼吁与其他社团组织和政党一同制定法律,让残疾人士得有工作的空间和机会[23]。
尼科·阿甘波拉在他所写的关于这个创举的故事《不可践踏梦想(Vietato calpestare i sogni)》一书中指出,他的创举虽然具原创性和革命性,但也可以想象并非没有困难和痛苦,他写道:“我之所以接受写这本书,目的在向我们自己和向众人重申‘不可践踏梦想’:为此,你们不要期待这是一本有关自闭症的专论,而是阅读一个不可思议的冒险故事,它源自于渴望缔造一个更美好、更包容、更关怀的世界而尽绵薄之力。你们将会看到我们的辛苦、挫折,以及惊讶和喜乐、友谊和爱心。我只不过是一个患自闭症孩子的父亲,开辟了一个提供给其他患者工作、尊严及前途的场所”[24]。
这些乃是实例,它们指出创伤如何能变成为关怀与接近受苦者的缘由,让受害者本人在别的受苦者身上找到更有益于自己的有效帮助。
- 参见 V. Caretti – G. Craparo – A. Schimmenti (edd.), Memorie traumatiche e mentalizzazione, Roma, Astrolabio, 2013, 169 s. ↑
- 参见P. Janet, L’état mental des hystériques, Paris, Alcan, 1911, 528. ↑
- 参见 V. Caretti – G. Craparo – A. Schimmenti (edd.), Memorie traumatiche e mentalizzazione, cit., 171. ↑
- 参见L. Goldberg, «The structure of phenotypic personality traits», i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 (1993) 26-34. ↑
- 参见S. C. Kobasa – S. R. Maddi – S. Kahn, «Hardiness and Health: A Prospective Study»,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 (1982) 168-177. ↑
- B. Bettelheim, Un genitore quasi perfetto, Milano, Feltrinelli, 1997, 59. 另参见A. Oliverio Ferraris, La forza d’animo. Cos’è e come possiamo insegnarla ai nostri figli, Milano, Rizzoli, 2004, 78-81. ↑
- J. Bolwby,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Affectional Bonds, London, Tavistock, 1979, 129. ↑
- F. Furedi, Il nuovo conformismo. Troppa psicologia nella vita quotidiana, Milano, Feltrinelli, 2008, 158. ↑
- E. A. Swedo et Al., «Prevalence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mong U.S. Adults – Behavioral Risk Factor Surveillance System, 2011–2020», in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n. 72, 2023, 707–715. ↑
- 参见M. A. Bellis et Al., «Life Course Health Consequences and Associated Annual Cost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ross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in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vol. 4, 2019, e517-e528. ↑
- M. T. Merrick et Al., «Vital Signs: Estimated Proportion of Adult Health Problems Attributable to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on – 25 States, 2015–2017», in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vol. 68, 2019, 999-1005. ↑
- 生活才能(life skills)指藉着适当的教育予以加强或在成长过程中使之成熟的生活技能。这些才能对身心压力和一般的生活困难有所帮助,使人得以掌控这些状况(参见G. Cucci, L’arte di vivere. Educare alla felicità, Milano, Àncora – La Civiltà Cattolica, 2019, 170-172)。 ↑
- 参见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hild maltreatment», 19 settembre 2022, in 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child-maltreatment ↑
- 参见B. Cyrulnik, Autobiografia di uno spaventapasseri. Strategie per superare un trauma, Milano, Raffaello Cortina, 2009; B. Van der Kolk, Il corpo accusa il colpo. Mente, corpo e cervello nell’elaborazione delle memorie traumatiche, ivi, 2015; C. Herbert – F. Didonna, Capire e superare il trauma. Una guida per comprendere e fronteggiare i traumi psichici, Trento, Erickson, 2020; J. L. Herman, Guarire dal trauma. Le conseguenze della violenza. Dall’abuso domestico al terrore politico, Roma, Giovanni Fioriti, 2024. ↑
- D. J. Siegel, Mindfulness e cervello, Milano, Raffaello Cortina, 2009, 31. Cfr G. Cucci – B. Varghese, «La terapia dei pensieri. La ripresa di una pratica antica», in Civ. Catt. 2023 II 26-37. ↑
- 参见 V. Caretti – G. Craparo – A. Schimmenti (edd.), Memorie traumatiche e mentalizzazione, cit., 183 s. ↑
- 同上, 177; testo leggermente modificato. ↑
- F. Shapiro, EMDR. Desensibilizzazione e rielaborazione attraverso movimenti oculari, Milano, McGraw-Hill, 2000, XII. ↑
- 参见前5 s; 224-227. ↑
- I. D. Yalom, Teoria e pratica della psicoterapia di gruppo,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1997, 30. ↑
- A. Galli, «Fragilità. “Orfana di mio figlio, così sopravvivo”», in Avvenire, 25 febbraio 2024. L’associazione si chiama A.M.A. Auto Mutuo Aiuto Ceprano (www.amaceprano.org). ↑
- https://fondazionegiulia.org/; 参见 G. Cecchettin – M. Franzoso, Cara Giulia. Quello che ho imparato da mia figlia, Milano, Rizzoli, 2024. ↑
- 参见 G. A. Stella, «PizzaAut, un’avventura gioiosa: l’entusiasmo batte i pregiudizi», in Corriere della Sera, 7 aprile 2024. ↑
- N. Acampora – E. Soglio, Vietato calpestare i sogni. La straordinaria storia di PizzAut e dei suoi ragazzi, Milano, Solferino, 202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