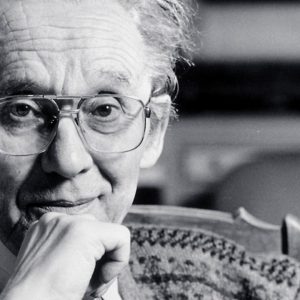美是相对于它的创造者而言
圣经用一种比希腊思想更深刻的方式展现“美之循环”(circolarità della bellezza):它从未被誉为一种孤立的属性,而总是与其他事物相关[1]。一个受造物之所以能被称为“美的”,单单因为它分享了天主的美和智慧,它是天主的美和智慧的鲜活反映。美的这种多面性在语义层面上便可见一斑。
希伯来词,tôb,既指美,也指善、真理、效用,以及无数与其语义相关的概念:“令人愉悦的、兴奋的、令人满意的、舒心的、有利的、实用的、合适的、正直的、有用的、丰富的、匀称的、芬芳的、仁慈的、宽容的、幸福的、诚实的、勇敢的、真正的,等等”[2]。这个词在希伯来圣经共出现741次之多;而希腊版的七十贤士译本(LXX)则用三个不同的概念来翻译tôb:agathos(善的)、kalos(美的)、chrēstos(有用的)。Kalos,这个词在新约中出现100多次,而且,它与agathos基本上是同义词[3]。
圣经虽然没有明确探讨形而上学的内容,但却承认美与存在的超越性特征有着深刻关联:美与生俱来地就与生命伦理、认知和决策息息相关,通过其魅力指示智慧之道。因此,美具有“象征性”的特征;以无声而雄辩的方式,通过自身的存在言说其创造者:“造化工程,如同一本书的文字,通过秩序与和谐指示其造物主和上主”[4]。
这种象征意义也在希伯来字母代码(gematria)中得到解读,字母代码是圣经思想中一个固有的特征,通过数字(组合)解读一项宇宙基本实相所隐含的象征性。希伯来词,tôb,在第一部关于创世的叙述中出现了七次(参阅:创1:4、10、12、18、21、25、31),象征造世工程的完整和圆满结局,这绝非巧合。由tôb串联起来的这七句话如同一首名副其实的副歌,吟诵并诠释天主计划的完美;任何事物,一经祂的手便皆为美好:“受造之物的美/善,并非受造后的修饰,却纯属造化(工程)之法则”[5]。
因此,tôb 根植于万物之所是。美,虽然与其欣赏者的愉悦、喜欢之感受相关,但却不是主观之物,仿佛取决于个人的品味和偏好,也并非源于那些能够领悟它的人所具有的鉴赏力,相反,美作为万物的内在属性,是对天主之渴望的表达:“[tôb] 这个词出现七次,而且与天主的八项事工相关:根据拉比传统,此概念并非用于描述第二天的工作,因为在第二天,天主将水与水、天与地分别开来,这似乎与统一、和谐的美(之标准)相矛盾。但其真正的概念意涵是,创造是美好的,因为源自由上而来的诉求和渴望”[6]。
另一个与美密切相关的要素是“惊叹”,它恰好与习以为常、无所谓和肤浅(仅此而已)的态度截然相反,这是将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之人持有的态度。造物工程令人称奇的地方——无论从数量还是完美程度上——是无穷尽的:“物各有所长,互成其美;天主的光荣,谁能看够?”(德 42:26)。
在圣经作者看来,对造化工程的完美和绮丽发出的惊叹,就是对创造者最真实的正名,造物主如同艺术家一样,将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恰如其分:“上主并未允许圣者讲论祂的一切奇事,全能的上主建立了这些奇事,为叫天地万物愈发显扬自己的光荣 […] 祂井然布置了自己智慧的伟业,祂从永远直到永远常常存在;对祂,什么也不能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祂不需要任何人的计谋。祂的一切化工,是多么美妙!所能见到的,只是一点火花”(德42:17,21-23;参阅:智11:21b)。
然而,对于美的模糊性,尤其是当它脱离真和善时,也不乏批评性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因着本身意义的丧失,美便成为毁灭的缘由。美是通往天主的道路,但它也可能引诱、误导人,使人无法领悟其创造者的用心,以至于崇拜受造物。万物的美是至高造物主(magis)之反映,象征着那位万有之技师在艺术、天赋和慷慨方面的“超凡卓越”:在这个象征意义中蕴含着祂的真理和良善。圣经作者虽然谴责这种舍本逐末的严重性,但似乎也理解人,而且,几乎要为那些堕入其中的人辩护,因为他们被映入眼帘的光彩所迷住:“如果有人被这些受造物的美丽所吸引而将其视之为神明;那么,他们就应知道:这些美物的主宰更是美丽,因为,全是美丽的唯一根源所创造的”(智13:3)。大自然的和谐与完美是美的最初体现,因为它们带有天主的印记,是造物主的美好品质之标识和印记。对万物之美的惊叹如此也就转化为感恩和赞美。
所有这一切都将我们导向另一个与美密切相关的主题:礼仪和表现美的艺术作品所塑造的一个神圣空间,在这个空间,所有受造物—人类作为其代言—都与天主关联在一起,天主希望万物都能参与祂的救恩计划:“在‘艺术创作’中,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展现自己是‘天主的肖像’,而人首先通过塑造自身人性中卓越的‘材质’来完成这一使命,然后练习用创造性的思维来管辖置身其间的宇宙。这位神圣的艺术家以慈悲的俯就态度,将祂超凡的智慧火花通传给人类艺术家,召叫他分享祂创造的大能”[7]。
恶之存在
苦难与邪恶的奥秘不会抹去造物之美。在《约伯传》精彩绝伦的结尾部分(参阅:约38-39章),十六组伟大的复沓诗句歌颂了天主(造化)工程之蓝图,对这计划人无法企及:太阳的运行轨迹、深渊的深邃、雪库、海洋的疆界、水生怪兽,以及鹳鸟辨识时间韵律的神秘能力 …… 因此,在约伯面前,(受造界)无限的广阔与无限的渺小如同幻灯片般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一闪而过,面对这一切,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无力评判。智慧的奥秘性纷繁复杂,在其无数的受造物中一览无余,也提醒人,他没有资格评判它们:受造界的纷繁复杂所展示和暗示的“超越”维度,启示了那位远超一切智慧和智识的“超群卓越者”(tanto più)。因为人并非这般智慧的标尺。
在新约中,耶稣被公认为“所做的一切都好 [kalos]”(谷 7:37),而且,他的言行完全一致。耶稣的宣讲邀请人透过奇妙多样的受造物默观天主的临在,与此同时,也默观天主之国深不可测的奥迹。自然之美成为智慧认知的终点——之所以是智慧的,因为谦卑,深知自身的有限,这智慧认知就在于懂得对物之所是发出惊叹。这种反差常见于福音比喻:种子唯有死去才能结出果实,甚至结出百倍的果实;小小的芥菜籽可长成参天大树;田地里的宝藏、价值连城的珍珠,等等。
耶稣将自己比作“好/善” [kalos] 牧人(参阅:若10:11,14),这与他的外貌无关,却因为他是“良善的”,他愿意为自己的羊舍命(字面意思是:为羊“舍身犯险”,这是一个至死不渝的行为)。“死亡”可能在一瞬间发生,甚至容不得人有真正思考的时间。这位善牧之所以愿意为羊舍命,完全出于对群羊的爱,所以,他不断地让自己应对死亡和危险。美象征着忠贞、温柔的爱情,这份爱是无伪的,甚至愿意为所爱之人付出一切。
爱至成伤的美
我们已经看到,美如何沦为操纵、自恋和放荡的牺牲品,最终导致毁灭[8]。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唯有苦难与善良,才能让美免于这致命的危险,才能让美彰显其真正的价值,从而将人从傲慢中拯救出来[9]。因此,善良与苦难是可能的救赎之美的表达:两种看起来对立的事实,在十字架的两根横木上找到了唯一交汇。
这种落差感在礼仪庆典中也得到证实。正如恩佐·比安奇(Enzo Bianchi)所指出的,奇怪的是,耶稣显圣容,这个最能体现美的庆日,恰逢日历上一个“不祥”的日子:8月6日(东西方少数几个同一天庆祝的节日之一)是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日子;由于阴历的原因,这一天常常与圣殿被毁的日期重合,第一次(公元前586年)和第二次(公元70年),几乎都在同一天:“真正的基督教美学不回避历史,而是肩负历史,并开辟出具有意义的愿景;不抹除痛楚和苦难,却与众人同甘共苦;不消灭罪恶,而是宽恕。基督教之美学含有先知性和怜悯。基于此,它是一种普世性语言。这种语言无需文字,却需信徒的见证”[10]。
这令人费解的部分也许是《圣经》和其他见解最大的不同之所在,后者更倾向于安慰人,或给出精确而详细的答案;这本书(圣经)似乎并不害怕会惊吓到读者,而且,邀请读者就他感到不舒服的地方进行对话:有时也可能是一个冲突或迷茫的对话,但读者却可以从中重新发现自身的真相。
耶稣显圣容的情节本身包含着与此相关的多重教导。在这个事件中,天主性生命的光辉被提前彰显出来,从而激起了伯多禄的惊讶和着迷(“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然而,紧随其后的报道却是耶稣首次宣告自己的苦难、死亡和复活,在这个预言中,耶稣揭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使命(参阅:玛16:21;谷8:31;路9:22)。这份崇高(高山)之美的启示既体现在十字架的晦涩中,也体现在逾越之光的荣耀中:在四福音书中,这两个件事始终有着紧密的延续性。天主性的美即使在被否定的情况下依然闪耀,因为没有什么能将其熄灭。
耶稣显圣容的经验本身呈现出这两个面向:既令人眼花缭乱,又令人惊恐不安,其中融合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神显独有的两种特质:惊颤(tremendum)和着迷(fascinosum)[11]。圣史们的报道已经详细说明,面对这种令人震撼的经验,宗徒们百感交集,既有惊讶和欣羡,也有六神无主、不安和恐惧。但是,主安慰了他们:“门徒们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遂前来,抚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玛17:6-7)。这一切也被15世纪的希腊画家费奥多尼斯(Teofane il Greco)创作的诺夫哥罗德显圣容像(Trasfigurazione di Novgorod)艺术性地完美呈现。画中,梅瑟和厄里亚站在山顶上,仿佛处于一种颤颤巍巍、痛苦的平衡之中,而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则身形后倾:其中一人甚至双手捂脸,仿佛在说,大博尔山的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超出了他们的悟性和能力。
即便是犹太传统也无惧那些看似否定美的事物:这是因为在美中所隐藏的最深层次的真理就源于正视相悖和不安。不妨想想《光辉之书》(Zohar)的神秘思想,天主从世间隐退(对此,不妨参考基督教秘契神学的“灵性的黑夜”主题)。这种隐退是对不可言说、无法描绘之事物的指涉。它是对美、梦想和乌托邦所唤起的怀旧之情;是一种对圆满的向往,而现今的我们所能管窥到的也不过惊鸿一瞥。美放弃了它本有的力量和威严,转而变为温柔,成为受难者悲戚和软弱中的亲密。美也是卡巴拉(Kabbalà)文本所提及的上主的名号之一:“在天主身上,Rachamim(仁慈)或Tif’ereth(美善)是一组同义词,因为以色列的天主本质上是一位富于怜悯和温柔的天主”[12]。
希伯来传统,不仅在圣经书卷中,例如,著名的“上主的仆人之歌”(依42:1-4;49:1-6;50:4-9;52:13-53:12),将空虚自己作为默西亚的主要特征,因为他将肩负人性的一切,特别是人的脆弱和不堪。“据巴比伦塔木德所载,有一天,拉比耶书亚·本·肋未(Rabbi Yehoshua ben Levi)遇到了先知厄里亚,于是询问说:‘默西亚什么时候来?’;厄里亚答说:‘你去问他罢’。又问说:‘那么,他在哪里?’;答说:‘在罗马城的城门口’。接着问道:‘有什么标志能认出他吗?’;答说:‘他与穷人、与患病的人坐在一起,当这群人一次性地将全部(伤口的)绷带拆解、重新包扎时,而他却一次性地只拆解和包扎一处(伤口的)绷带。他的理由是:‘或许我(启示自己是默西亚的时间一到了)就该走了,免得拖延’”。另外,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也忆起儿时听过的一个犹太传说:“在罗马城门口坐着一个患麻风病的乞丐,他等待着,那是默西亚”[13]。因此,默西亚并不显眼,也不会因其颜值而惹人注目,相反,却是隐藏自己、默默无声。
读到这些描述,人们不禁会联想到耶稣受审的过程:面对来自多方面的指控,他保持沉默(参阅:玛 26:63;27:14)。这位被圣经誉为“世人中最为美丽的”(咏 45:3),却因痛楚、苦难和背叛而面目全非,甚至失去了人的面貌,如此应验了《上主仆人第四首诗歌》那令人生畏,同时,从文学的角度,又是最崇高和感人的预言:“他没有俊美,也没有华丽,可使我们瞻仰;他没有仪容,可使我们恋慕。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真是个苦人,熟悉病苦;他好象一个人们掩面不顾的人;他受尽了侮辱,因而我们都以他不算什么。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我们还以为他受了惩罚,为天主所击伤,和受贬抑的人”(依 53:2-4)。
耶稣的美,不魅惑人,也不引诱人,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美,这是穿透苦难和绝望的深渊后,所展现出的一道任何事物都无法抹去或遮蔽的光亮。圣奥斯定在一篇精彩的讲道中,将十字架两臂交汇的两种矛盾元素融合为一,以解读道成肉身的奥迹: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启示的美和自我空虚。唯有耶稣基督能使对立因素合而为一:“两支号角吹出不同的声音,但却是同一圣神在它们内吹气。第一支号角咏唱:容貌俊美,胜过一众人子;第二支号角与依撒意亚同频,欢奏:我们看见他,毫无俊美,也毫无华丽。两支号角是由同一圣神所吹奏,因此它们的乐律并没有不和谐。你们不要从声响上排斥它们,却要尽力领会其中神韵 […]。他毫无俊美,也毫无华丽,为的是赐给你们俊美和华丽。何为俊美?何为华丽?是纯爱之爱,为的是你能在爱中奔跑,在奔跑中去爱”[14]。
基督的十字架以刻骨铭心的方式彰显了天主之美的有悖常理:“反对的记号”(路2:34),“外邦人眼中的愚妄和绊脚石”(格前1:23)。甚至从美学角度来看也的确如此。事实上,基督的十字架打破了黑格尔哲学中企图演绎的以人为美的艺术范畴。然而,就连黑格尔那般才华横溢之人,也不得不承认被钉十字架上的基督有着令人不安的美,尽管这种美无法被归于理性范畴。“我们不能用希腊美的形式来描绘基督受鞭打、头戴刺冠、背负十字架走向刑场、被钉、在漫长而痛苦的折磨中就死。然而,这些情境的优越性源于神圣本身、内在深度、作为精神永恒时刻的无限痛苦、以及顺服和属天的平安。以这个形象为核心,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团聚一起 […]。与古典美不同,非美在这里如同一个必要的时刻”[15]。
十字架之美的“争议性”维度
被钉的基督如同绊脚石一般的奥迹,以张开的双臂,渴望将所有的敌对力量吸引汇聚到他那里。天主之美既不魅惑人,也不囚禁人,而是使人重获自由,并让人能够辨识出那永不消逝、亘古长存的事物;正因如此,对这违背常理之事件的惊叹,可转化为对更伟大的智慧者之拥抱。
即使是文学作品,也毫不掩饰地强调了与天主相关的美、审美和悖论之间的关系:唯有谦和的美才具有救赎的效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那句名言“美将拯救世界”——如今几乎成了一句口号,每当触及美的主题时,它准会出现——在小说中,二者间却从未有直接关联。从上下文语境来看,这句话根本不像严肃的名言警句或振聋发聩的训言,以至能让人从中受益匪浅。恰恰相反,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年轻人伊波利特对主人公梅什金(“白痴”)的嘲讽,这位年轻人口中宣泄着所有的愤怒,因为他还不到二十岁,却因肺结核而濒临死亡。通过如此的反抗情绪,他道出了对这个充斥着不公、痛苦、疾病、死亡之世界和生活方式的抗争:“王子,您真的说过美能拯救世界吗?听着,先生们”,他用洪亮的声音对众人喊道,“王子说美能拯救世界!我敢说,他之所以会有这种天真的想法,是因为他坠入了爱河。诸位,王子恋爱了……但是,什么样的美能拯救世界呢?”[16]。因此,凡是这样说的人都是自欺欺人,一个天真到做白日梦的人,一个被多愁善感的妄想所困扰的人。
梅什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谦卑而朴实地保持沉默,因为没有任何言语能够承受其重。美并不与痛楚和苦难隔离开来,相反,在包容这一切的同时,在让自己变成惹人爱怜的温柔的同时,展现其最动人的一面。梅什金的沉默影射基督的沉默,“唯一绝美的存在”,而梅什金正是基督的化身[17]。
伊波利特的话语虽然带有反抗的情绪,却也寄托了对救赎之美的追求。因为这个问题不能成为我们最终的答案,这个答案注定在虚无中回响。卡尔洛·玛利亚·马蒂尼枢机(Carlo Maria Martini)在一篇精美的牧函中,开宗明义地,以美为题,不吝笔墨地言及这份沉默,集中探讨经由比较而来的不言自明之美,并展现了美的本质:“仅仅痛惜和谴责我们所处之世界的丑陋是不够的。对于我们这个幻灭的时代,仅仅谈论正义、责任、公共福祉、牧灵计划、福音诉求也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闪耀出生命中真实与正义之美,因为只有这种美才能真正俘获人心,使人归向天主 […]。梅什金的沉默仿佛在说,拯救世界的美,就是分担苦难的爱”[18]。
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逆转,是天主的圆满启示——借用路德的名言来说,就是“sub contraria specie”(隐藏在悖论的外表之下)——在玛利亚的谢主曲(Magnificat)中,这份隐藏在悖论外表之下的天主的启示方式得到了最成功的颂扬(参阅:路1:46-55)。正是天主的这种行事风格让乍看之下似乎对立的事物变成美好,因为祂能让掉价的重新升值,同时也批判人将所领受的恩赐绝对化的傲慢(“祂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祂曾使饥饿者饱飨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路1:52-53)。
奥斯定惊讶地瞻仰着被钉十字架上的基督,从中认出了爱的最高举动,为所爱之人竟也不怕全然地牺牲自己,甚至就死,由此彰显了被钉的基督真正的美。“天主是美丽的,圣言与天主同在 […]。圣言在天上是美丽的,在地上也是美丽的;在母胎中是美丽的,在父母怀抱中也是美丽的;在奇迹的彰显中是美丽的,在承受苦难时也是美丽的;在被邀请进入生命时是美丽的,在无视死亡之际也是美丽的;在舍弃生命时是美丽的,在重获生命时也是美丽的;在十字架上是美丽的,在坟墓中也是美丽的,在天上同样美丽。你们要以聪慧的心聆听这首颂歌,不要让肉身的软弱使你们的目光偏离祂美丽的光华”[19]。
与被钉的基督的相遇会改变那些默观它的人,因为在默观中祂的生命和美被通传给仰瞻祂的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是:即便面对生活的艰辛,祂的忠信始终无坚不摧。在十字架前,众人被邀请去做克苦,净化自己的眼目、感官和思维方式。这是皈依的第一步:“苦修所造就的并非‘好’人,却是具有‘美’的人,圣人的与众不同之处绝不是‘善’,因为‘善’也可能存在于属血肉的人和罪大恶极之人身上,而圣人却独有灵性之美,这是发光和光明磊落之人所闪耀的夺目美,也是庸俗和血肉之人绝对无法企及的美”[20]。
只要离开(十字架的)这个拥抱,双方的对立因素将继续分裂,互相抗衡、威胁和争斗。
让人安心的美
十字架的事件,虽有悖常理,又史无前例,却并不否定它的美。就连艺术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西班牙沙勿略城堡(Castello di Xavier)的小圣堂里,有一幅画,描绘的是被钉十字架上的面带微笑的基督:他的面容动人而祥和,所诠释的正是主耶稣在福音书中所言及的独有品性——良善、心谦(参阅:玛11:29)。这是基督在最痛苦、最卑微的时刻,向他身边的所有人传达的至高信息:他拥有一个无人能夺走的秘密;无论是痛苦、孤独、羞辱、愁苦,甚至死亡都不能将这个秘密从他身上夺走。那微笑所反映的是他与天父亲密无间的秘密,而天父也渴望将自己通传给所有人。
最重要的是,与被钉十字架上的基督对话,尽管十字架描绘的是一个饱受痛楚和不公摧残的人,但身悬十字架上的基督却异常平和,竟还能将生命从刑架和死亡之地传递出去。对圣依纳爵而言,最重要的抉择,以及最终的确认,总要在十字架前达成:“如果说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不像样的、负面形状的圣像——尚有美可言,那恰恰揭示了天主拥有将一切负面因素在祂内消化掉的无限能力。被高举的基督,将所有的暴风雨——无论袭击对象是主的门徒们,还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都引向自己”[21]。
十字架的语言,以其残酷的本质,表露的却是一份爱情的忠贞宣言;尽管死亡和苦难无法否认,但也无法将这份爱抹去。十字架的语言述说的是更进一步的愿景,这愿景质疑,也挑战着虚无主义的诱惑。
- Cfr G. Cucci, «Le caratteristiche della bellezza», in Civ. Catt. 2024 IV 237-246. ↑
- Cfr H. J. Stoebe, «tôb, buono», in E. Jenni – C. Westermann (edd.), Dizionario Teologico dell’Antico Testamento, vol. 1, Torino, Marietti, 1978, 566. ↑
- Cfr G. Ravasi, «Bellezza», in R. Penna – G. Perego – G. Ravasi (edd.), Temi teologici della Bibbia,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10, 128. ↑
- Atanasio di Alessandria, s., Oratio contra Gentes, 3, in PG 25, 69. ↑
- C. Westermann, Genesis 1-11, Minneapolis, 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 1987, 166. ↑
- G. Ravasi, «Bellezza», cit., 17 s. La parola de–siderio significa letteralmente «mancanza della stella». ↑
- 若望保禄二世,给艺术家的一份信,1999年4月4日,n. 1。 ↑
- Cfr G. Cucci, «Le caratteristiche della bellezza». ↑
- Cfr A. Giannatiempo Quinzio, «Quale bellezza salverà il mondo?», in N. Valentini (ed.), Cristianesimo e bellezza. Tra Oriente e Occidente, Milano, Paoline, 2002, 86. ↑
- E. Bianchi, «Editoriale», in Parola Spirito e Vita, n. 44, 2001, 7. ↑
- Cfr R. OTTO, Il sacro, Milano, Feltrinelli, 1966, 22-42. ↑
- A. Giannatiempo Quinzio, «Quale bellezza salverà il mondo?», cit., 90. ↑
- Ivi, 92 s. 巴比伦塔尔木德的引文出自Sanhedrin, 98a; 布伯的引文则出自:M. Buber, Sette discorsi sull’ebraismo, Roma, Carucci, 1986, 16. ↑
- Agostino d’Ippona, s., In Epistolam Ioannis, 9,9; cfr Id., De bono viduitatis, 19,24. ↑
- G. W. F. Hegel, Estetica, Torino, Einaudi, 1967, 604. 另参,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也曾这样评述格吕内瓦尔德(Grünewald)的《伊森海姆祭坛画》,“望着基督的身体,我毫无泪流满面的困顿,那具躯体的恐怖状态对我来说仿佛是真实的,在这个真相面前,我明白了为何其他的十字苦像(画作)令我局促不安:美,改变了容貌。这种改变容貌的美只应属于天使的歌咏团,却不适合十字架”(E. Canetti, Il frutto del fuoco. Storia di una vita 1921-1931, Milano, Adelphi, 1982, 235)。 ↑
- F. Dostoevskij, L’idiota, in Id., Romanzi e taccuini, vol. II, Firenze, Sansoni, 1963, 470. ↑
- Cfr T. Todorov, La bellezza salverà il mondo. Wilde, Rilke, Cvetaeva, Milano, Garzanti, 2010, 244. ↑
- C. M. Martini, «Quale bellezza salverà il mondo?», in Id., La bellezza che salva. Discorsi sull’arte, Milano, Àncora, 2002, 104; 103. ↑
- Agostino d’Ippona, s., Enarrationes in Psalmos, 44, 3. ↑
- P. Florenskij, La colonna e il fondamento della verità, Milano, Rusconi, 1974, 140 s. ↑
- P. Sequeri, L’estro di Dio, Milano, Glossa, 2000, 6. 另参:依纳爵·罗耀拉,《神操》,53-54号:“设想我面对悬在十字架上的我主耶稣,向祂祈祷。我请问祂:怎么以造物主之尊降生成人,又怎样以永远的生命而接受现世的死亡,甚至是为我的罪而这般惨死!我再转看我自己:我为基督做了什么?现在为基督做什么?将来为基督应该做什么?眼看祂这样被悬在十字架上,尽量激发善情、善念。对祷应是自发的谈话,就如朋友与朋友,仆人与主人谈心一样;有时祈求某项恩宠,有时承认自己犯的某项罪过,有时诉说自己的困难,并请求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