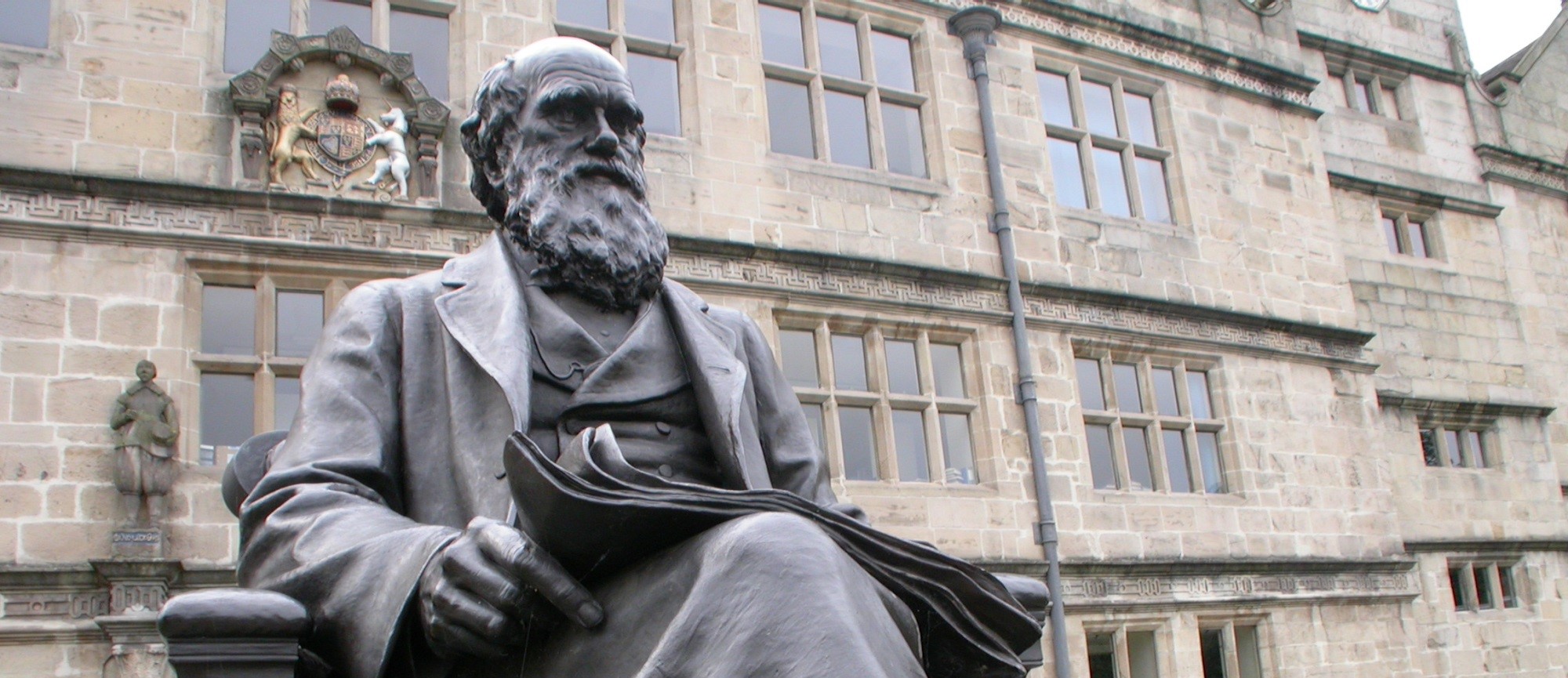达尔文在意大利
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是查尔斯∙达尔文(1809-82)的第二部主要作品,在此12 年之前年问世的《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2]是其第一部最著名著作。通常,这两部作品被公认为达尔文的“代表作”。这种观点虽然使这位伟大研究者的许多其他科学巨著相形之下略显失色,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动物学还是植物学领域,它们都是生物学历久不衰的必读经典。然而,上述两部著作之所以独放异彩,是因为它们彻底改变了关于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起源和人类自身起源的思想。
英文版的《物种起源》问世后,很快便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甚至于1896年被翻译成日语)。在意大利,尽管《理工学院》(Politecnico)期刊曾经在1860年刊登过对原文的评论,但达尔文的名字并未引起注意:在那个年代,国家统一问题才是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焦点。其它的都不被关注,但也有一个例外,即动物学家斐理伯∙德∙斐理比(Filippo De Filippi,1814-67),他于1864年将达尔文的理论编入自己在都灵大学的课程中,并在同年中推动都灵出版商博卡(Bocca)完成了《物种起源》意大利文译本的首版首印[3]。
尽管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并未在意大利学术界引起轰动,但它埋下的种子很快便生机盎然:《人类的由来》一经问世,当年就被立即翻译和发行,成为于都灵出版的第二部意文版达尔文著述[4]。进化论不可逆转地从都灵迈入了意大利。
在那些年间,《公教文明》尚处于出版工作的初期(该期刊于1850年创刊,早于《物种起源》9年,早于《人类的由来》21年),围绕科学与信仰的关系这一广泛主题,它充当了与达尔文作品展开对话的主角,发表了一系列有趣的对比和批评。为此,籍《人类的由来》出版150周年之际,我们在回顾达尔文思想传入意大利的同时,特别忆及它与当时我们的《公教文明》期刊的关系。在这方面,斯德望∙贝尔塔尼(Stefano Bertani)2006年的一项研究可以提供很大帮助,使我们通过《公教文明》的文章,对十九世纪进化论的讨论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5]。
达尔文:生物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达尔文不仅引导了十九世纪西方生物学和思想的巨大变迁,而且对我们的整个宇宙观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为了能够充分理解这一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他生活的时代,无人质疑受造物种恒常不变的信念。那时候,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仍广为流传,包括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创始人卡洛∙林奈(Carl Nilsson Linnaeus,1707-78)也对此深信不疑:“现今存在的各物种数目与起初‘无限实体’所创造的物种数目一样”[6]。
其实,关于物种进化可能性的想法在此之前已经出现。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1744-1829)是第一个发表关于物种可变性解释理论的人,他当时提出的是一种“演化论”。这位学者认为,环境是导致物种器官组织变化的原因;此外,他的另一个假设是物种本身从某种程度上具有演化的“意愿”。
但是,拉马克的这一论点并不被科学界所接受。其中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是著名的法国学者、古生物学的创始人乔治∙库维尔(Georges Cuvier,1769-1832)。这位学者维护当时基于不容置疑的创造主义的“不变性”理论:上主是所有生物物种的创造者。在发现已灭绝物种的古生物化石后,为了解释其中一些物种的灭绝,他提出了气候或地震大灾难引发的灾灭论:每当一个大灾难发生,就会导致某些动物物种的灭绝。
达尔文熟知拉马克和库维尔的理论,然而,随“贝格尔号”帆船在南美海域的长期航行(1831-36年)使他勘察到许多古生物和现有物种比照的现象,也导致他彻底脱离了物种不变论(以及相关的灾灭论)和拉马克式的物种演化论。
根据达尔文《自传》[7]中的记载,早在1838年,他就已经确信受造的物种并非不可变异的,但尚不能够对变异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在私下里与他许多要好的同事们畅谈,但从来没有得到认可。对此,达尔文曾这样写到:“人们常说,《起源》的成功表明‘这个议题已经传开了’,‘人们的思想已经准备好接受它了’。我却不以为然,因为虽然我不时向许多自然学家探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对物种稳定性表示怀疑”[8]。
尽管如此,达尔文对自己的直觉深信不疑,他继续独辟蹊径,寻求物种变异现象中可能存在的自然规律。他在阅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的著作《论人口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9]之后深受启发,于是假设,物种有可能根据“自然选择”的机制进化,为生存而竞争(struggle for life),其结果是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达尔文熟悉养殖者和农民对生物(动物和植物)进行“人工选择”的机制,这在当时又称 “驯化”。虽然达尔文曾对此进行长期研究,但在阅读马尔萨斯的文本之前,他从未把这种人工技术原理与“自然条件中” 存在的法则挂钩。虽然进化机制的原理一直若隐若现地隐藏于他的理解中,但直到学习马尔萨斯的社会学理论,他才恍然大悟。
1838年,达尔文觉察到这一机制时“茅塞顿开”的感觉不啻一个真正的“尤里卡效应”(Aha-Erlebnis)。他在《自传》中叙述说:“1838年10月,也就是在着手系统性研究的15个月之后,我出于个人喜好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书。由于对动植物习性的长期观察,我对每个生命为生存而进行的争斗有相当的认识基础。这本书立刻使我联想到,在竞争条件下,有利的变异趋向于被保留,而那些不利的则会被淘汰,其结果是可能形成新物种。一个理论的雏形于是浮现于我的脑海中,但是,由于生怕里面会掺有任何成见,我决定在一段时间内不做任何笔记”[10]。
此后不久,这位科学家就意识到,不仅动植物,人类的由来也同样可以在这一范畴中进行研究:“在1837年或1838年,我一认识到物种确实是可以变异的,就马上不由自主地想到,人类应该也受同一法则所支配。于是,我愉快地就这个问题做了笔记。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未曾考虑发表这些内容”[11]。的确,直到30多年后的1871年,这一见解才被公布出版。
1838年的初步推测在几年后(1842年后)得到了新的启示,这让科学家自己都感到惊奇:从物种分类的属、科、亚目等级别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地点和自然条件,物种在各自的适应和专门化程度下逐渐分化。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分类学这一概念。事实上,它不仅对应生物的形态学性状,同时也是显示物种对其历史、地理和环境所做反应的明确秩序。难怪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没有识别出来[…]:这明明就是哥伦布立蛋”。这就是他的第二个超级“尤里卡效应”。这一发现对达尔文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他这样写道:“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马车跑到了哪里:霍然间,问题的答案浮现于脑海里,令我喜出望外”[12]。
达尔文在知识、社会和宗教方面的审慎态度
达尔文并不热衷于哲学,更不喜欢形而上学,他与后者从年轻时展开的思想斗争[13]一直持续到晚年:“我极不善于冗长的抽象思考,不可能在形而上学方面取得好成绩”[14]。尽管存在这样的困难,但他非常了解用以解释物种变异性的“元因”和“次因”概念之间的区别:“最有权威的科学家似乎一致认同每个物种均被独立创造这一假设。在我看来,根据我们对造物主赋予物质的法则的了解,以下假设似乎更为恰当:自古至今,地球生物的产生和消亡取决于次因,诸如那些决定个体出生和死亡的原因。当我并不将所有的生命视为特殊受造物,而是长期生活于寒武纪系统较早的那些地层沉积之前的少数生命的直系后代时,我似乎看到它们的进化”[15]。
因此,达尔文认为,新物种是自然选择法则这一“次因”的产物,而“次因”是造物主这一“元因”所愿意的:“生命这一概念具有宏大的内涵和不同的力量,它最初由造物主印在几个形式中,或是唯一的一个形式中”[16]。
实际上,达尔文从未对生命的起源进行纯理论性研究,例如,事实上,关于生命起源于无机物的观点,我们在其著作中根本找不到他对造物主之必然性的质疑。对他来说,这是些无用的理论,与他发表的科学性辩论无关。事实上,在1859年,他只想争取科学界对自然选择法则的认同:他为迈出这一步准备了20余载。
这一论点在《物种起源》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达尔文通过不懈地观察,列举了无数实例对其加以说明。如上文所言,达尔文其实在1838年便已相信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但并未在1859年的著作中揭示这个观点:他意识到有关此议题需多加慎重,担心阐明这一论点的人类学结果会分散公众对进化机制这一真正发现的关注。也就是说,提出人类由来这一重大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
我们通过达尔文的《自传》得知,出于有意识的选择,他在第一部著作中偶尔旁敲侧击地触及了此问题[17]:“尽管我在《物种起源》中从未针对任何一种特定物种的衍生进行讨论,但是,为了避免有人指责我隐瞒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最好补充说,这部作品‘可能会对人类的由来和历史带来一些启示’。在不具备任何论证的情况下,空谈对人类起源的看法将对这本书的声誉有害无利”[18]。
此后,他又花费了12年的时间,通过观察来收集和整理论据,借此构建他对人类起源解释理论的基础。在此,达尔文展示的真正科学家风范至今令人赞叹,他认真对待科学工作,毫不吝惜资源和时间,只求结论的严谨可信。真正伟大的科学发现往往需要科学家花时间使其发展成熟,特别是在涉及范式性转变时更是如此,比如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
然而,使达尔文迟迟拿不定主意的并不仅仅是科学原因:他也同时意识到文化、社会和宗教领域隐藏的暗礁。对此,他在一些手稿中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我并不认为这卷书中阐述的观点必然会扰乱到任何人的宗教信仰”[19]。实际上,他很清楚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自然选择法则在挑战创世主义,而创世主义基础是:圣经中记载的启示性真理同样涉及自然科学领域。
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包括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其他诠释学、圣经或神学方面的参照。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从他在《自传》中的详细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科学家人生旅程中一种不可知论的倾向。早在“贝格尔”号帆船的长期航行中,他已开始显露出一些有关的根本性质疑。
值得赞赏的是,虽然达尔文越来越不相信创世主义的解释,但这并未妨碍他对科学研究目标的追求。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达尔文仍只能相信那位未识之神,而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祂因不可触及、不可理解的宇宙的浩瀚而受人尊崇[20]。应该指出的是,这位科学家从未将这方面的个人观点与其科学研究和刊物相混淆。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不愧一位名副其实的科学家。他从不愿涉足科学或生物学以外的辩论,也从不使用没有科学依据的论据。
我们知道,达尔文在1871年已成为一个完全的不可知论者。从《人类的由来》中一个篇幅很长的段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只是从生物学家的角度思考有关神的问题。达尔文希望把人的宗教性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生物学现象,而不是对神存在与否的验证:“对神的信仰不仅经常被视为人与低等动物之间最主要的,而且也是最全面性的区别。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可能证实这样的信念是人与生俱来或本能性的。另一方面,对无所不在的精神体的信仰似乎具有普遍性,而且表面看来与人类理性的巨大进步有关,尤其是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和惊奇感等能力的飞跃。我知道,对神的本能信仰被许多人用以证实祂的存在,但这种说法有欠妥当:因为这容易导致我们去相信种种稍强于人的残暴恶神的存在。事实上,对后者的信仰远比对仁慈神灵的信仰更普遍。普世而仁慈造物主的概念并不天生就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除非人通过长期的文化熏陶得以升华”[21]。
对达尔文思想的接受
我们认为,达尔文有意识地将自己局限于纯科学范畴,这一举措对学术界接受进化论假说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科学家朋友和同行对这一学说表现出极大热情,包括已经赫赫有名的自然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95)。达尔文很快便成为新一代生物学家的灯塔。在浓厚兴趣的推动下,关于进化论假设及其机制的大量新研究和刊物在随后的数年中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达尔文一心避免引起公愤,他希望与当时的学术界和科学界对话,最大限度地展现其进化论科学意义之重大。无疑,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在《物种起源》中回避了这一思想的最终人类学后果:如果他提出的进化机制得到认可,人类进化也将归属同一进化规律,并因此将人的起源追溯到猿。
正如我们所见,对于达尔文,这一推断虽然早在1838年就显而易见,但因缺乏坚实的科学证据而需要另行专门研究。然而,达尔文这种谨慎的保留态度并未得到生物学家朋友们的理解,他们纷纷开始在科学和公开辩论中揭示他的进化论框架的人类学结论。由此,这些理论立刻遭到支持英国圣公会的伦敦资产阶级圈子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引爆了达尔文本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公愤。
因此,《人类的由来》出版后,关于人由猿来的公开辩论一触即发,速度之快,白热化、公开化以及激烈程度完全出乎达尔文的意料。当时,这种名副其实的思想交锋冲破了公共领域和学术圈的界限,即使在非专业性期刊中也屡见不鲜。
在19世纪下半叶的文化和政治氛围中,哲学界和知识界中的反神职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是在关于人类起源的辩论中对进化论思想最热心的捍卫者:这毫不奇怪,他们在自然选择理论中发现了可以服务于其宗旨的有力论据。特别是在德国,达尔文的理论立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那些年里,自由主义者正在推动以反天主教为特征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
然而,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这种激烈的争论在意大利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阿尔卑斯山似乎同时在地理和文化意义上构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屏障。为了理解当时的情况,只需注意到,《公教文明》于1858年设立了一个题为《自然宇宙论与创世纪的比照》的新专栏,为反思圣经宇宙观与科学成果之间的摩擦提供空间。1860年,以主张科学与圣经之间的“协和”立场而闻名的物理学家詹巴蒂斯塔∙皮安恰尼(Gianbattista Pianciani)神父发表了一篇关于《物种的毁灭和创造》的专题文章,其中,他对拉马克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并在结论中指出它尚未被证实[22]。
只有瑞士科学家弗朗索瓦∙朱尔∙皮克泰∙德拉里夫(François Jules Pictet de la Rive,1809-72)在他的一篇批判性评论中谈到了达尔文及其理论,文章作者所主张的阶段创造(Le creazioni successive)论与库维尔的理论相近。德拉里夫指出,在达尔文的理论中,“已确定和观察到的事实与从中得出的归纳性推理不相对应。[…]而皮安恰尼神父重新着手于‘事实’和直接观察结果的立场则确立了《公教文明》在随后年代中的方向,当时,关于人类起源、演化论(Il trasformismo)和实证科学方法的辩论愈演愈烈”[23]。
后来,这种“事实”和“归纳推理”之间的不对应成了整个20世纪科学界的批判对象。然而,这显然是一场认识论和方法论性质的争议:进化论是一种假设,还是描述了一个被证实的事实?
1978年至1982年期间,当本文作者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进修生物学时,这种讨论依然非常活跃。当然,遗传学和古生物学在20世纪中的发现为达尔文的论点带来了众多有利论据。总的来说,这所大学的教授们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应被视为具有某种程度可能性的优秀理论,但无法得到肯定性的证实。
今天,许多生物学家在自然选择理论中加入了另一种机制,即影响物种进化的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当一个物种的种群数量大幅度减少时,会产生怎样的情况?许多在大种群中可能消亡的特征可能会成为在一个小种群中占主导地位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种群数量大幅减少的事件对达尔文假设的严格的自然选择机制做出了补充。
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情况对达尔文提出的物种进化的刻板进程所造成的一系列影响是出乎意料和不可估量的。由此可见,鉴于“科学”是从数据的“数学”结果而得出的一种假设,我们无法奢望它能够在生命一类的复杂问题上拥有最终话语权。不断涌现的新发现将持续推进我们对各种现象的进一步认识。
随着第二部代表作《人类的由来》的出版,人们对达尔文思想的接受态度产生了极大转变,扩散到意大利的影响随即将《公教文明》期刊卷入了这场波澜。期刊并未通过对达尔文刊物的批判性研究投入到有关争论,相反,它所发起的思想斗争所针对的是那些年来自于德国轰轰烈烈的文化斗争。当时的天主教文化处于困难时期,鉴于该期刊的性质和使命,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编辑部所采取的决定,尤其是本雅明∙帕隆巴(Beniamino Palomba)神父的作品。“帕隆巴所回应的问题,从其根源上来说,既不属科学也不属哲学领域,然而此问题却迅速表现为政治与意识形态上针对教会的公开对抗”[24]。帕隆巴希望捍卫教会和意大利,使其免受一种新生的科学宗教的影响。这种科学宗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同时有害于科学和宗教的可悲的败坏。
达尔文以科学为唯一依据的选择
通过简要回顾历史上人们对达尔文著作和理论的接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哲学和政治领域对其理论的利用和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身处反对西方基督宗教的论战之中,达尔文正直的科学家风范令人称赞。事实上,这种历史遗存至今仍显现于许多辩论中。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在达尔文1889年去世后创立的“达尔文主义”[25],以及兼容遗传学新发现的“新达尔文主义”流传之广,以致于当代人士误认为达尔文是一位实证主义哲学家,一位仅在科学中寻找真理和生命问题秘诀的社会政治潮流的开山鼻祖。于是,科学理论被其他学者转化为“主义”,这种“达尔文主义”显然不可能不令人质疑。对此,达尔文本人会有何想法?我们现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至今,一些科学家继续谈论达尔文理论,他们无法抵抗意识形态化的诱惑,将他们的科学视为超越专业科研范围的“真理”。例如,著名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发表自己的科研成果之余,试图通过它们将一切宗教信仰的表达形式嘲讽为蒙昧主义。当然,我们并不质疑他的生物学作品的价值–因为除了博学之外,他还兼具良好的文学技巧——但许多当代作家表示,在其论述中,各种超越科学研究范围的断言使他的态度显得倨傲无礼。可以说,他宣传的是达尔文的思想,而绝非其美德。
让我们回顾一下达尔文本人的话:“我很高兴能够依照多年前莱尔(Lyell)给我的建议行事,这使我避免了种种争议。当时,对于我在地质方面的工作,他强烈建议我不要因为争论而自找麻烦,因为这些争论通常只会消耗自己的时间和感情,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26]。达尔文的这一观点和行事方针在其所有刊物、众多信件及《自传》中始终如一。他一心专注于科学研讨,尽管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在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学术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同时代人的影响,但他始终坚持与这些领域保持距离。
关于这种科学和道德的严谨性,也许最知名的例子是达尔文在1880年对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1818-83)的答复。那时候,马克思对自然选择理论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和“必要的”阶级斗争的“生物学”基础。他请求达尔文以批判态度审阅《资本论》第二卷,并希望将这部著作献给他。对此,达尔文回复如下:“感谢阁下惠函及附件。至于您对我的作品发表的评论,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无需本人同意。[…]我希望不要将相关部分或整卷书献给我(尽管蒙此殊荣令我由衷感激),因为这将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我对整部作品的认可,而我实际上对它并不很了解。虽然本人坚决支持在所有问题上的思想自由,但在我看来(无论对错),对基督宗教和有神论的直接攻击对公众影响甚微;科学进步对人类理性的渐进式启蒙更有助于促进思想自由。鉴于以上原因,我在写作中始终回避宗教,不超越科学的范围。[…]很抱歉不得不拒绝您的请求”[27]。
耐心、谦逊与和善:达尔文的美德
毫无疑问,达尔文始终密切关注着有关人类进化及由来的学术辩论,尤其是通过不同作者在1859年至1871年期间发表的许多刊物;但是,他保持缄默逾30载,埋头以自己的科学方法分析这个难题,尤其是深化了对哺乳动物的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动物行为学的比较研究。对此,他这样写道:“但是,当我看到许多自然科学家完全接受物种进化的学说时,我感觉完成笔记并发表一篇关于人类起源的论文似乎时机已到。我很高兴着手于这项工作,因为它终于使我有机会全面展开一直非常吸引我的话题,即性选择问题”[28]。
这位科学家在等候传播其创新思想的契机。耐心等待和把握时机是他为人处世的典型特征。的确,在《人类的由来》中,我们将发现如此广泛的论证范畴,其中极为有趣的研究领域涉及许多动物中存在的二形性、《物种起源》中很少涉及的性选择、以及大量举例论证和论述。
此外,达尔文还撰写了一篇关于人类和动物情感表达的专题作品[29]。在常年的“沉默”期间,他在研究中积累的大量笔记很快便促使他致力于第三本著作的编写。一年之后,他在1872年出版了这部作品。这是关于进化论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无论是篇幅,还是对自然和人类学观察的描述及分析,他的三部著述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达尔文于此展现的风格可以说是“近乎痴迷”,他致力于了解和发现各种现象的一致性,从他本人及其同事所做的无数自然观察中探索相应的法则。
达尔文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使他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在自然科学和科学史发展中的重要性,然而,他特有的谦逊态度至今仍令世人钦佩。这种谦逊不仅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也源于一种自觉和理性的诚恳。事实上,遗传学在那个时候尚未出现[30],但达尔文意识到了这一点:“至此为止,我不时谈及的变异——在家养状况中的生物中既常见又多种多样,在自然情况下的生物中程度较轻——好像一概由偶然因素造成。这显然是一种完全欠妥的说法,但它有助于我们坦率承认对所有特定变化导因的无知”[31]。
非但如此,达尔文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的谦卑更令人感叹。在此,我们希望以一个美好的见证来结束本文,并以此再度向这位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人致敬。对于一个总是处于激烈辩论和争议焦点的人(只需回顾当年那些重要报刊将达尔文描绘为诸如猿人或动物园驯兽师的各种漫画等等),我们不能不为他对许多同事和其他批评者的豁然宽容态度所折服。即使他们往往不失严厉,对他展开公开批评和科学辩论,达尔文总是能够虚心接受。他将这一切视为推动其思想和研究的一臂之力。在达尔文笔下,我们仅偶遇到这种态度唯一的一个例外,不过仍不失高雅和幽默:“至于我的评论者,必须承认,除了那些不值一提的缺乏科学知识的人,我几乎受到了所有人的公平对待。我的观点经常被极不准确地报道,或遭受严厉的批评和嘲笑,但我觉得总体上都是出于善意。唯有米瓦特(Mivart)先生是一个例外,一位美国人评价说,他像一个‘无能律师’ 一般地对待我,赫胥黎认为他像个‘老贝利律师’。然而,总体而言,我的作品总是被过誉”[32]。
-
Cfr Ch.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and the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London, John Murray, 1871(本文对达尔文的引用使用意文版:L’originedell’uomo e la selezione sessuale, Roma, Newton Compton, 2017)。 ↑
-
Cfr Id.,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859 (本文对达尔文的引用使用意文版:L’origine delle specie,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2011)。 ↑
-
经达尔文准许后,由乔瓦尼∙卡内斯特里尼(Giovanni Canestrini)和路易吉∙ 萨林贝尼(Luigi Salimbeni)编辑的意大利文版通过摩德纳的扎尼切利(Zanichelli)和都灵的博卡(Bocca)出版社首次出版。 ↑
-
1871年,米歇尔∙莱索纳(Michele Lessona)负责翻译的意文版由Utet出版社发行。 ↑
-
Cfr S. Bertani, «La “Civiltà Cattolica” nel dibattito sull’evoluzionismo ottocentesco», in Annali di storia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12 (2006) 89-122. ↑
-
C. Linnaeus, Fundamenta Botanica, Amsterdam, Salomon Schouten, 1736: «Species tot sunt diversae quot diversas formas ab initio creavit infinitum Ens»; Id., Philosophia Botanica,Stockolm – Amsterdam, G. Kiesewetter, 1751: «Species tot numeramus, quot diversae formae in principio sunt creatae». ↑
-
Cfr Ch. Darwin, Autobiography, London, John Murray, 1881 (本文对达尔文的引用使用意文版:Autobiografia [1809-1882], Torino, Einaudi, 2016)。 ↑
-
同上,第105页。 ↑
-
该文本于1798年在伦敦首次出版,并在1826年之前发行了另外几个修订版。 ↑
-
Ch. Darwin, Autobiografia (1809-1882), cit., 101 s. ↑
-
同上,第112页。 ↑
-
同上,第102页。 ↑
-
参见同上,第66页。 ↑
-
同上,第122页。 ↑
-
Ch. Darwin, L’origine delle specie, cit., 551. ↑
-
同上,第552页。 ↑
-
同上,第501页:“还有什么比以下事实更独特的吗?人的手适于抓握,鼹鼠的爪适于掘土,同样,马的腿,海豚的鳍,蝙蝠的翅膀,都是出于同一模式的构造,由类似的骨头组成,相对位置也一样”。 ↑
-
Id., Autobiografia (1809-1882), cit.,112。达尔文从《物种起源》的倒数第二页摘录了这句话。 ↑
-
Id., L’origine delle specie, cit., 544.。 ↑
-
CfrId., Autobiografia (1809-1882), cit.,67-77. ↑
-
Id., L’origine dell’uomo e la selezione sessuale, cit., 454; 另见第849页。 ↑
-
Cfr G. B. Pianciani, «Distruzione e creazione delle specie», in Civ. Catt. 1860 V 55-76. ↑
-
在这一段和下一段中,我们简要地总结了脚注5中所注明的S. Bertani的一些研究成果。 ↑
-
Ivi, 6. CfrB. Palomba, «Le due contrarietà della teorica dell’uomo-scimmia», in Civ. Catt. 1871 IV 21-35. ↑
-
CfrJ. Hesketh, «The First Darwinian: Alfred Russel Wallace and the Meaning of Darwinism», in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 25 (2020/2) 171–184. Hesketh明确指出,这个概念最初于1889年被科学界接受时,具有哲学和科学意义的限定,只是在后来,文化领域又另外赋予它信仰的意义。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得以澄清。 ↑
-
Ch. Darwin, Autobiografia (1809-1882), cit., 108. ↑
-
G. Montalenti, «L’evoluzionismo ieri e oggi», in Ch. Darwin,L’origine delle specie, cit. ↑
-
Ch. Darwin, Autobiografia (1809-1882), cit., 113. ↑
-
Id.,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London, John Murray, 1872. ↑
-
由孟德尔(Mendel)于1866年发现并发表的遗传规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科学界忽视,否则它可以帮助达尔文更好地奠定进化论的基础。 ↑
-
Ch. Darwin, L’origine delle specie, cit., 202. ↑
-
Id., Autobiografia (1809-1882), cit., 107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