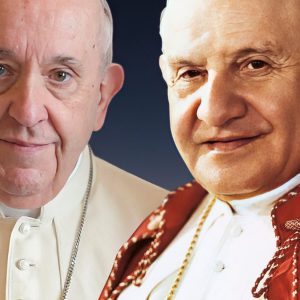“20世纪的许多杰出文学形象都出自弗兰兹·卡夫卡笔下。在某一天清晨醒来时变成了一只甲虫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无故被捕的约瑟夫·K。一个希望被认可的土地测量员。某一刑法部门及其附属官员”[1]。他的姓氏甚至已化为一个形容词,诸如:卡夫卡式处境、卡夫卡式场境、卡夫卡式经历,等等[2]。
去年正值卡夫卡去世一百周年。然而,作为20世纪最具神秘色彩的作家之一,弗兰兹·卡夫卡究竟是何许人?他是一个缺乏连贯性的作家,体现其才能的并非某一部作品,而是他所创作的整体作品。对此,与其同时代的卡夫卡的崇拜者约翰内斯·乌尔齐迪尔(Johannes Urzidil)这样写道:“ […]在布拉格发展起来的格式塔(Gestalt)理念[…]使我们能够观察和理解一个文学面貌的奥秘,其迥然不同的流派汇集在一起,应运而生的是一种无法分析的整体美” [3]。
生平
弗兰兹·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出生于布拉格,于100年前的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去世。倘若一位作家能够通过不同人物和形象来描绘整个社会以映射其本质,那么这位波希米亚作家可谓以登峰造极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任务。毫无疑问,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我们可以将他的作品定义为幸存之作,因为禁受住了作者的销毁欲[4]与纳粹的迫害[5]。卡夫卡是中欧环境的代表,在奥匈帝国疆域内形成、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融汇了不同文化、语言、民族及宗教。
卡夫卡的家庭是那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交汇的一个典范。他的母系来自洛维(Löwy)家族,它体现着这个富裕的犹太裔德国资产阶级家庭有文化且敢于冒险的一面;父系卡夫卡家族则是一个相形之下较为贫穷和普通的捷克裔犹太人无产阶级家庭。父亲赫尔曼(Hermann)是一个在极贫困条件下白手起家并取得稳固经济地位的人。他决定让儿子在德国学校接受从小学直到人文高中的教育,这也是受到提升其社会地位之驱使的缘故。事实上,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语言在当时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分界线:在当时的45万居民中,会讲德语的只有34 000人。从属于德语飞地那时意味着成为在布拉格社会中掌握权势与责任的少数群体的一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语言因素在决定卡夫卡写作的某些特征方面并非次要的,无论如何,卡夫卡毕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德语和捷克语双语作家之一。
卡夫卡整个一生都是在布拉格的几个街区和离家最近的居民区度过的,而且,大部分时间都与家人在一起,因为直到35岁他才从父亲家里搬出[6]。布拉格的氛围与得天独厚的地貌在其笔下随处可见,“细致入微”,在这位作家故去后,这座城市将成为永远的“卡夫卡之城”[7]。在读完德语人文高中后,作家于1901年报名进入法学系学习。他其实本想就读文学系,但因父亲的反对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在试读化学专业两周之后最终决定改读法学。1902年,卡夫卡结识了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勃罗德不仅成为他的朋友与支持者,而且将是其文学遗作的管理人。
1906年6月,毕业后的卡夫卡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开始了为获取检察官头衔所必需的为期一年的实习阶段。1907年10月,培训期满后,他开始在通用保险公司(Assicurazioni Generali)任职。在获得梦寐以求的使其独立于家庭供养的经济自立后,渴望拥有充足时间进行写作的想法却与其日常文职生活的节奏产生了冲突[8]。因此,短短九个月之后,他便辞去了该保险公司的工作,并于1908年8月就职于波希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保险公司,直至1922年才因健康状况而提前退休。在保险公司工作期间,卡夫卡多次因公外出。对波希米亚工厂的访问使他亲身体验了工人们常常处在非人的工作条件,在这一点上,卡夫卡是许多同时代作家中的一个例外。
在家庭中,弗兰兹所接受的是一种肤浅而形式化的宗教教育。对此,他在多年后的《致父亲的信》中有所抱怨。成年后,他渴望深入探究自己的犹太血统。1910年至1911年间,他通过使其感到与自身情感相契的意第绪语戏剧而重新接触了家族宗教。1915年,他还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他并不赞同新兴的犹太复国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好奇之后,他并没有加入其中,尽管事实上他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加深了解,甚至曾在1923年动念迁居巴勒斯坦,但实际上那不过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
于1917年确诊的肺结核随着岁月流逝而日益恶化,这位作家在日记和书信中称其为“创伤”。在那些年,卡夫卡曾四处游历,并多次前往疗养院和休养地调治自己欠佳的健康状况。其中在苏劳(Zürau)度过的期间最长,在那里,住在自己深爱的姐姐奥特拉(Ottla)家中的卡夫卡创作了《蓝色八开笔记本》。1923年9月至1924年3月,卡夫卡在柏林居住的数月中肺病恶化,因而被马克斯·勃罗德和他的医生朋友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Robert Klopstock)紧急送回布拉格,并于4月被送往维也纳附近克罗斯特纽堡(Klosterneuburg)附近的基尔林(Kierling)住院治疗。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在那里去世。
人生的选择:文学创作还是婚姻?
传记作家克劳斯·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认为,这位作家在1912年做出了他的人生选择[9],自此,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卡夫卡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写作和文学创作,放弃了他曾多次尝试的婚姻计划,同时还背负着对“病态”的纯洁以及难以活出肉体亲密关系带来的压力。“女人,或者说得更无情一点,婚姻是必须面对的人生代表”[10]。这种紧张关系在《给父亲的信》以及大量书信与日记中显现出来,也在短篇小说《乡村婚礼的筹备》中得到了升华:一方面是对夫妻正常生活的展望;另一方面是既不愿分散写作的精力,也不愿因自己特殊的生活节奏而对未婚妻造成伤害,这种生活节奏是为了写作,而不是为了满足妻子的合理期望。
事实上,卡夫卡按照他自嘲地称之为“演习生活”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每一天[11]:“(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在办公室工作之后,卡夫卡会回到家里,从三点左右一直睡到七点半,然后与朋友一起或独自散步一小时,与家人共进晚餐(整个布拉格资产阶级都惯常于将晚饭安排得较晚),十一点左右开始写作,直到凌晨两三点,有时甚至更久”[12]。卡夫卡的创作既有高产期,也有长时间的枯竭期,二者交替出现。例如,在1912年秋天,他写下了《失踪者》的前七章(勃罗德在他去世后以《美国》为标题出版了这部作品)、《变形记》(其短篇小说中最著名的一部)以及他一鼓作气于1912年9月22日至23日夜间写就的短篇小说《判决》:这也许是在其所有短篇小说中他最喜欢的一部,他曾多次高声朗读给朋友听。
卡夫卡曾在1922年写道:“假如说我曾经快乐过(我不确定是否真的快乐过),即使在写不出东西以及与写作相关的一切,那时候我根本没有能力写作,所以一旦动笔,一切都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因为写作的灵感无处不在”[13]。这位作家甘愿努力将两种视角结合在一起,然而,“面对‘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选择(这也许无非是一种假定),他总是选择后者,但又不愿做出背弃生活的选择,这种情境于是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周而复始地进行着”[14]。因此,他与菲利斯·鲍尔 (Felice Bauer) 的婚约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他在1912年8月13日结识了这位保持了长期交往的女友,在1914年第一次与其解除婚约,经过第二次尝试后,两人的婚约于1917年被正式解除。卡夫卡人生中的另两位女性是格蕾特·布洛赫(Grete Bloch)和朱莉·沃里泽克(Julie Wohryzek),其中他与后者于1919年订婚并于1920年解除婚约。另一位重要的女性是米莱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á),卡夫卡将一些手稿交给了她,其中包括《失踪者》和(写于1919年11月)的《给父亲的信》,1921年,他又将从1909年开始写的《日记》交给了她。卡夫卡唯一与之一起生活过几个月的女性是多拉·迪亚曼特(Dora Diamant),那是自1923年9月至1924年3月期间在柏林。
文学创作
我们已经提到卡夫卡为写作而遵从的生活节奏是多么苛刻。这位在夜间写作的作家断断续续地进行文学创作,为文学而在所不惜,以至他在1922年7月写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将这种牺牲定义为“为魔鬼服务的报酬”[15]。他很好地表达了自己与写作之间的矛盾关系:“写作供养我,但它供给了我这种生活不是更为准确吗?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离开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加美好。恰恰相反,如果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糟,完全无法忍受,甚至会使我发疯”[16]。一切都是为了写作,其中也有对“未能如愿的人生”的恐惧[17]。对此,瓦根巴赫(Wagenbach)写道:“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这种对‘未能如愿’的人生的负罪感日益加重,随之而来的是对这种人生的‘虚无的恐惧’,而能够对这种恐惧自圆其说的唯有写作。在此,必须明确区分的是卡夫卡对‘自然’生活的‘渴望’及其永不屈服于这种渴望的‘决心’。仅仅因为逆境,他才无法成为一个热爱家庭、善于交际的人,却被认为是一个圣人,这是不可接受的。所有(不胜枚举的)向这种怀旧情绪屈服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是因为人和环境,而是因为卡夫卡本人,在他看来,成功对于一种专心致志于文学的人生而言不过是 ‘辅助性建筑’而已”[18]。
考虑到卡夫卡写作的不规律性、他对出版的抵触情绪以及他最著名的小说都是在死后出版的事实,再加上他的《书信集》和《日记》,仅后两部作品就长达3000页,这一切远远超过了他严格意义上的全部叙事作品,制定一部文学编年史并非易事。有的编纂者选择以作品的创作年代为基准,其他人则选择遵循作品的出版年代。
按照目前的结构选编的短篇小说集,我们可以区分出:《沉思》(其中收录了1904年至1912年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乡村医生》(收录了1914年至1917年的作品)、《修建中国长城的时候》(收录了1914年至1924年的作品)和卡夫卡曾编辑过的《饥饿艺术家》(收录了1922年至1924年的作品),但由于这些作品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才面世,所以他未能亲眼目睹出版。在从未被选入文集的短篇小说中,最著名的是1912年的《审判》、1913年的《司炉》、1915年的《变形记》以及1919年的《在流放地》。
卡夫卡死后出版的是以下三部著名小说:《判决》(1925年)、《城堡》(1926年)和《美国》又名《失踪者》(1927年)。埃尔维诺·波卡尔(Ervino Pocar)这样写道:“众所周知,卡夫卡不愿出版自己的作品,即使出版也是出于朋友的鼓励和推动,可以说几乎是朋友们强迫他出版。当决定出版时,他会催促出版商,并为确保顺利、迅速的出版工作而向其做出细致的指示;对此,只需阅读他与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的通信即可获知”[19]。
对于在其有生之年发表的作品,“短篇小说”一词并不总是恰当的术语。只有一部分作品才是如此,其余的则是散文、思绪与省思。然而,作者在生前形成的系列作品已经无法被分开[20]。
语言问题
卡夫卡与父亲的冲突和复杂关系往往被视为其叙事风格与诗学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纳迪娅·富西尼(Nadia Fusini)将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叙述的童年“阳台”插曲[21]作为所受教育的标志:一天晚上,作家因为耍脾气而被关在阳台上罚站。对此,卡夫卡写道:“坚持要水的执拗令人难以置信,但我当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还有被关在门外的惶恐不安,我始终未能正确理解两者间的合理关系。即使多年之后,我仍然为这样一种折磨人的幻想而感到恐惧:那个巨人,我的父亲,最后,会在半夜里无缘无故地走过来,把我从床上揪到阳台上,也就是说,我对他而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22]。福西尼认为,外界与内心之间对立的辩证关系是他与外部世界相处的特点,而这种关系正是源于他的上述经历:“与别人的每一次相遇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折磨”[23]。
尽管如此,那种尤其体现于其叙事中的距离感和疏离感,我们并不认为单纯归因于那些童年经历。在我们看来,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塑就了卡夫卡的独特风格。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位作家在布拉格生活的那些年中,这座城市的语言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在捷克语占主导的环境中,会讲德语的居民占比不过7%。语言障碍在那时“甚至是荒诞的”[24]。赫尔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让儿子在德语学校接受教育的选择,一方面使他归属于一个强大的社会少数群体,另一方面也训练了他使用一种具有绝对特殊性的语言。瓦根巴赫和约翰内斯·乌尔齐迪尔认为,布拉格德语实际上是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仿佛一个“实验室”的产物。布拉格德语是少数人在一种隔离的环境中使用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远离其他以德语为主的地区的日常用语,布拉格德语逐渐简化,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涩滞。卡夫卡在其作品中所使用的德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已经将作家与其犹太血统及重要的生活背景中分离开来。
“离开布拉格,就无法想象卡夫卡作品中那些不同寻常的题材、以精简文字打造出的明快语言,以及他(卡夫卡)特有的纯粹主义。德国人在布拉格与世隔绝,可以说是现代异化的先声,这对作品的主题至关重要:德国人的确在社会中占据了所有重要职位,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占比仅为7%的极少数”[25]。
许多布拉格作家在这种社会孤立的特殊条件的驱使下,在语言和处于社会边缘的“极端”人物的选择上精心打造出了一种巴洛克式、沉重的怪诞异国风情:“杀人犯、麻风病人、皮条客、变态人、酒鬼、鬼魂、替身、瘾君子、白痴、小人”[26]。卡夫卡的散文以精准、冷峻、简洁的风格为特点,吸引了这座城市中时而积极时而消极的知识分子对他的关注,这种选择也是出于布拉格德语的状况。“这是一种贫瘠的语言。虽然这种‘布拉格德语’的纯正性被许多城市居民视为无与伦比,但它不仅在发音上,而且在结构上,尤其是在词汇上皆与标准的德语相去甚远。事实上,在孤立的重压下,布拉格德语日益成为享受国家资助的节日习语。那时候,词汇的消失显而易见”[27]。在寻求真理的驱使下,卡夫卡不得不使用在他的环境中学会的德语。然而,这也决定了“卡夫卡对事物的疏离也是由语言因素造成的。[…]在语言中始终残留着出入,每个单词之间的差异也自然存在”[28]。
与卡夫卡生活于同一时代背景中的布拉格的约翰内斯·乌尔齐迪尔对这种特殊的语言条件作出了一种积极的评价:“我们的布拉格德语遭受过多的指责,它当然不是不存在口音,但却丝毫没有方言的印记,之所以能够自中世纪以来在这个语言孤岛上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正是因为它未曾遭受外省及地区环境那些具有缩合元音及混合发音倾向的方言的影响。这对于文学而言是一大幸事,因为我们布拉格德语人群曾经并将继续以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进行写作。[…]这种日常用语和文学语言之间的完美契合也许正是以卡夫卡为代表的布拉格作家在形式及相似性上所取得的成果的最强大秘密”[29]。
某些关键词语:“距离-排斥”、“内疚-无能”
关于卡夫卡的研究不计其数。对卡夫卡作品的阐释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费尔迪南多·卡斯泰利(Ferdinando Castelli)神父早在1962年就在本刊撰文指出,对卡夫卡作品的阐释不仅与读者的历史和情感相吻合,而且也取决于这些因素。如果说文学作品是由其读者完成的,因为他们会在自己的头脑和内心中“重写”文本,那么对于卡夫卡而言更是如此。关于这位波希米亚作家笔下的信仰维度,卡斯泰利神父曾这样写道:“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们有必要首先指出,稍后还会重复,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带有令人不安的模糊性和双重意义的情节、表达方式与时刻。同样,这种情况也涉及超越性的基本要素,其中包括天主、救赎、恩典、永恒、启示,等等。因此,根据读者对这些时刻的敏感度和不同的审视态度,他们可能会从中看到一个向天主敞开的空间,看到一个并未表达的‘是’,或是看到一种挥之不去的难以超越的、沉重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他无法冲破围墙,跨越隘口”[30]。
依照我们的观点,我们希望强调某些体现卡夫卡写作特点的关键词语,其中第一组是“距离-排斥”。
卡夫卡写作时与现实保持着谨慎的距离。仿佛他就在一堵玻璃墙后面。他所呈现的是一种透明性,是以目光和文字的精准性将他“从现实中撕扯下来”置于一种暂停的时间性之中,在那里,永恒就像是时间的停滞,将行动和思想环抱于其中。许多短篇小说中并没有前后之分,只有瞬间的体现。“他的用词不会添加任何内容,最多不过是在一种重复中加以暗示,但这种重复也并不是一种评论。卡夫卡的故事,总是被正确地宣布为像谜一样的故事,具有荷马史诗般的难以捉摸。众生与万物自行呈现,没有参照物,仅仅是存在于自身的语言表述中” [31]。
卡夫卡是一位以零度展示现实的作家,他借助文字的力量而使事物存在。他的孤独,如同恶毒的新娘,被选中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将这种孤独付诸笔下并呼唤读者去完成。从这个角度看,卡夫卡并非一位象征主义作家:是文字本身作为一个强有力且不容置辩的象征展现于读者面前,它们需要诠释、评论和判断。卡夫卡是一位文字与意象的作家,他的文字与意象就像《变形记》中的甲虫一样,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海中。对于这一生动的头脑中的形象,卡夫卡在写给他的出版商沃尔夫的信中极度担心它不会以任何形式出现于封面上[32]。乌尔齐迪尔这样写道:“他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意象的价值。每一个隐喻所包含的内容总会超出作者意于表达的内容,因为一个图像有其自身的独立存在,而且,当它是真实而准确时,这一意象会从自身延伸出一些意义,而在它出现的时候,这些意义可能尚无任何外部参照和动机”[33]。
他的作品揭示了现实似乎“只是”在它被描述的时刻所展现的超越性维度。 “叙述对于卡夫卡而言即是命名,是在赋予其每一事物自身的最终语言个性的同时将其展现出来”[34]。超越的事物只能被暗示,因为它无法被占有,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被占有,因为只有掌握在手中的才可能被占有[35]。“语言只能andeutungsweise (“暗示性地”),即以影射的方式运作,而绝不应在比较的模式下运作(vergleichweise,“比较地”)”[36]。卡夫卡曾断言:“对于超越感性世界的一切,我们只能使用纯粹影射式的语言,甚至绝不能使用类似于比较的方式;这是因为语言本身所涉及的只是占有[即Besitz,卡夫卡合理的说法]及其关系”[37]。
在《蓝色八开笔记本》中,永恒轮回这一主题在许多片段中反复出现,尤其是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卡夫卡写道:“一切代表我的东西对我来说都过于狭隘,即使我本身的永恒对我来说也过于狭隘。但是,如果阅读一本好书,比如一部游记,那么我就会被唤醒,感到满足,对我来说便已足够。这证明我之前并没有将这本书纳入我的永恒,或者说我没有深入到这本书必然包含的永恒的影射范围中”[38]。作者使用了所有时态,但只有现在时似乎是一致的、存在的。“卡夫卡因此揭示了那些潜在的、隐秘的事物,这要归功于一种空隙语言,这种语言由那些只知道其当下显现的名字组成”[39]。
卡夫卡之写作是为了生活,因为投之笔下的文字可以使他从不安的、在踌躇和严格苦行下度过的日子里重获新生。“卡夫卡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相信这是他生命的唯一方式,也就是说,唯独如此,他才能接受人生”[40]。
其次是“内疚-无能”。卡夫卡是分析内疚感的大师,无论这种内疚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是外部施加的还是自我强加的。在《致父亲的信》中,关于内疚的转述是多重的,既有由父亲而引起的无边内疚,又有与两人关系并不相干的内疚感。在有过错的同时又是无辜的。因此,在我们看来,与其说我们引用了其中某些段落的《致父亲的信》是一部自传体作品,它似乎更是一部富有诗意的宣言,以至那封信从未被寄出,因为在一些年之后,就连卡夫卡本人也认为它言过其实。纳迪娅·富西尼甚至表示那完全是“杜撰”出来的[41]。
作家的负罪感源于他未能达到父亲和世界的期望,未能按照人们对他的期望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虽说心理和教育因素具有其重要性,但最终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人生奥秘,那就是卡夫卡在赋予父亲世界的角色的同时改变了父亲的形象:“你对我来说就是万物的尺度”[42]。
有罪是因为无能,无能是因为有罪。1912年的短篇小说《判决》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作品,因为它不仅以绝对的方式表达了卡夫卡与亲生父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卡夫卡与自己的关系。这篇短篇小说展示了他如何体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并由此而感到自己受到谴责。至于这些主题是如何在两部伟大的未完成小说《城堡》与《判决》中表达出来的,无庸在此赘述。
卡夫卡是宗教信仰作家吗?
吉多·索马维拉(Guido Sommavilla)于1992年在本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我们希望重申一些事实、文本和论据,在我们看来,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布拉格-德国犹太作家根植于犹太-圣经和/或基督宗教传统所具有的深厚的宗教信仰”[43]。索马维拉所考虑的文学作品是《109条箴言》,又称《祖劳箴言》,摘自我们已经提到的《蓝色八开笔记本》。这些片段篇幅长短不一,从几行到一整页不等,其中汇集了思想和反省的火花[44],通常是神谕式的,有时是叙事体,有时具有启发意味。由于无法对其进行任何可能的图式化,因此无法对其进行系统性介绍。对于它们,我们可以重温本文开篇所引用的乌尔齐迪尔的观点,他将卡夫卡的作品和思想视为一个格式塔作品全集:“ […]在布拉格发展起来的格式塔(Gestalt)理念[…]使我们能够观察和理解一个文学面貌的奥秘,其中不同流派汇集在一起,从而促生了一种无法分析的整体美” [45]。如果说根据索马维拉的精辟定义,这些作品果真“具有不可避免的神秘性”,那么我们也同样必须承认,在第三本和第四本笔记中的许多段落都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其中谈到了永恒、过错、堕落、伊甸园、罪,谈到了艺术、死亡、自由与创造,但很少涉及基督的形象:其中明确提及的有几处,其他地方则似乎是对《新约》背景的暗示。
此外,卡夫卡的朋友和崇拜者、基督徒作家古斯塔夫·雅努什(Gustav Janouch)在《与卡夫卡的对话》(Conversazioni con Kafka)一书中还提到了更多内容。我们与索马维拉一致同意卡夫卡并非是一位无宗教信仰和无神论作家的说法。然而,与其不同的是,我们倾向于对卡夫卡的宗教情感进行一种更为温和的解读,在经历了青少年时期关于宗教信仰的正规和社会学教育之后,他对犹太教的兴趣不仅在内心深处有感触,在生活中有实践,更多的是在成年时期的重拾。
伊塔洛·阿利吉耶罗·基乌萨诺(Italo Alighiero Chiusano)这样写道:“关于这一切的起源,我们又回到了假设,即人类机器诞生以来,就存在着‘在运转上存在问题‘或运转不佳的东西[…]。谈论‘原罪’让人感到不安,似乎意味着神圣和忏悔性质的讹诈。人们试图寻找另一种说法,但实质内容大致不变”[46]。在我们看来,基乌萨诺的直觉似乎照亮了这些片段中温暖且充满活力的“内核”,尽管是典型的箴言式散文,但这些片段往往更频繁地回溯和重温涉及堕落、罪和天堂的主题。
从大量的作品片段可以看出,卡夫卡是通过邪恶之谜,而不是通过创造的奇迹或对救恩历史的沉思,来探讨生命、自我和天主的意义。必须说,他的叙述传达了一种“存在问题的”超越[47] 。让我们引用几段文字来帮助读者“亲身感受”这些思想的强度,它们往往也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卡夫卡这样写道:“自堕落故事即将告终之际,伊甸园也有可能与人一起受到诅咒,但被诅咒的只是人,而不是伊甸园”[48]。然而,更加明智的却是以下这些片段:“对于人而言,有两种致命的罪,所有其他的罪都源于这两种罪:急躁和懒惰。急躁使他们被逐出地堂,而懒惰则使他们无法返回。但最致命的罪也许只有一个:急躁。由于急躁,他们被逐出(地堂);同样,由于急躁,他们无法返回那里”[49];或者:“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生命一样伟大,这一事实使它看起来好似无限”[50]。
关于“堕落”和“被逐出地堂”这一主题,由于在卡夫卡的传记中、在他与父亲以及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中具有存在主义的意义而显得是一个他想要以特别的方式进行探讨的主题,但本文将仅限于引用以下四个片段。“我们之所以是罪人,不仅是因为我们吃了知善恶之树的果实,还因为我们尚未尝到生命之树的果实。有罪是我们所处的状态,与内疚感本身并不相干”[51];“就其本质而言,被逐出乐园是一个永恒的事实,与时间无关。虽然被逐出乐园是确定无疑的,世界末日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的永恒性(或者用时间的术语来说,这一过程的永恒重复)使我们有可能永远留在乐园之中,无论地上的我们是否知道这一点”[52]; “邪恶的令人悲痛的观点是:它认为仅凭我们对善恶的区分便足以管窥到我们与天主的相似之处。诅咒似乎并不会使其本质变得更糟:它将用肚子来衡量(生命)旅程的长短”[53]; “对人类堕落的惩罚存在着三种不同方式:其中最温和的方式是将其逐出地堂;第二种是摧毁地堂本身;第三种方式,也是最可怕的惩罚,是将其排除在永生之外,其他的都和以前一样”[54]。
因此,卡夫卡是一个受救赎问题“困扰”的人,他通过文学寻求救赎,因为他知道,或者说他让我们明白,文学(也许)传达的是另一种更广泛、更深刻的救赎。或许,在我们看来同样可能的是,想象卡夫卡在读完我们所写的东西后摇头轻言:“你们还是没有理解我”。
- K. Wagenbach, Kafka. Una battaglia per l’esistenza, Milano, il Saggiatore, 2023, 9。这本书是关于卡夫卡生平信息的主要来源。 ↑
- Milan Kundera在In qualche posto là dietro一文中对专制国家的“预言”进行了饶有趣味的反思。对此,我们不作报道,由于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如需阅读,可参见M. Kundera, L’arte del romanzo, Milano, Adelphi, 2023,第143-167页。 ↑
- J. Urzidil, Di qui passa Kafka, ivi, 2002, 12. ↑
- 众所周知,卡夫卡曾要求他的生前好友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销毁其尚未问世的作品,其中包括小说《失踪者》(又译为《美国》)、《城堡》以及《审判》等20世纪重要著作。幸运的是,这位作家“违背”了卡夫卡并在他死后出版了其所有著述。然而,那些诋毁勃罗德的人则将这些出版工作视为对卡夫卡遗愿的背叛。 ↑
- 20世纪40年代初,卡夫卡的女友多拉·迪亚曼特(Dora Diamant)所持有的手稿在柏林被没收并销毁。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后,他的图书和许多信件均遗失无踪,亲友遭到放逐,三姐妹埃利(Elli)、瓦莉(Valli)和奥特拉(Ottla)死于集中营中。参见K. Wagenbach, Kafka…, cit., 13。 ↑
- 卡夫卡主要是在暑假期间与马克斯·勃罗德结伴游历欧洲。他曾与这位好友一起于1909年前往加尔达(Garda)湖,于1910年去了巴黎,于1911年周游意大利北部并重返巴黎,于1912年前往魏玛。1917年被诊断患有肺结核之后,卡夫卡在布拉格以外的居留主要是在疗养院进行调治,以求康复。唯一一次的长期外出是从1923年秋至1924年春,卡夫卡在柏林与多拉·迪亚曼特(Dora Diamant)一起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数月光阴。1924年3月,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他被紧急送返布拉格。 ↑
- J. Urzidil, Di qui passa Kafka, cit., 167. ↑
- 参见短篇小说Poseidone。 ↑
- 参见K. Wagenbach, Kafka…, cit., 119-127。 ↑
- F. Kafka, Quaderni in ottavo. Alla ricerca del senso di sé, Roma, Il Pellegrino, 2024, 97. ↑
- 参见短篇小说La talpa。 ↑
- K.Wagenbach, Kafka…, cit., 134. ↑
- 同上,第127页。 ↑
- 同上,第149页。 ↑
- 同上,第125页。 ↑
- 同上,第124页。 ↑
- 另参见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 ↑
- K. Wagenbach, Kafka…, cit., 123 s. ↑
- F. Kafka, Tutti i racconti, Milano, Mondadori, 2017, V. ↑
- 同上,VII. ↑
- 参见N. Fusini, Due. La passione del legame in Kafka, Milano, Feltrinelli, 2024, 69. ↑
- F. Kafka, Lettera al padre, Milano, Feltrinelli,2023年,第14页。 ↑
- N.Fusini, Due…, cit., 69. ↑
- J. Urzidil, Di qui passa Kafka, cit., 14. ↑
- K.Wagenbach, Kafka…, cit., 77. ↑
- 同上,第82页。 ↑
- 同上,第83页。 ↑
- 同上,第86页。 ↑
- J. Urzidil, Di qui passa Kafka, cit., 20. ↑
- F. Castelli, «Le tre vertigini di Franz Kafka», in Civ. Catt. 1962 III 27-40. ↑
- N. Fusini, Due…, cit., 25. ↑
- 参见F. Kafka, Racconti, Milano, Mondadori, 1970, XII. ↑
- J. Urzidil, Di qui passa Kafka, cit., 29. ↑
- N.Fusini, Due…, cit., 24. ↑
- 参见F. Kafka, Lettera al padre, cit., 38. ↑
- N.Fusini, Due…, cit., 55. ↑
- F. Kafka, Quaderni in ottavo…, cit., 61 s. ↑
- 同上,第85页。 ↑
- N.Fusini, Due…, cit., 24. ↑
- 同上,第25页。 ↑
- 同上,第84页。 ↑
- F. Kafka, Lettera al padre, cit., 15. ↑
- G. Sommavilla, «Franz Kafka, uomo religioso?», in Civ. Catt. 1992 IV 52. ↑
- “他想要的更是思想的闪光,一种像雷电一样照亮健忘的现实的灵光一闪(Gedankenblitz)”(N. Fusini,《Due……》,引用如前,第27页)。 ↑
- J. Urzidil, Di qui passa Kafka, cit., 12. ↑
- F. Kafka, Lettera al padre, cit., 4. ↑
- 例如,可参见短篇小说《法律面前》及《皇帝的信息》。 ↑
- F. Kafka, Quaderni in ottavo…, cit., 74. ↑
- 同上,第37页。 ↑
- 同上,第71页。 ↑
- 同上,第73页。 ↑
- 同上,第64页。 ↑
- 同上,第74页。 ↑
- 同上,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