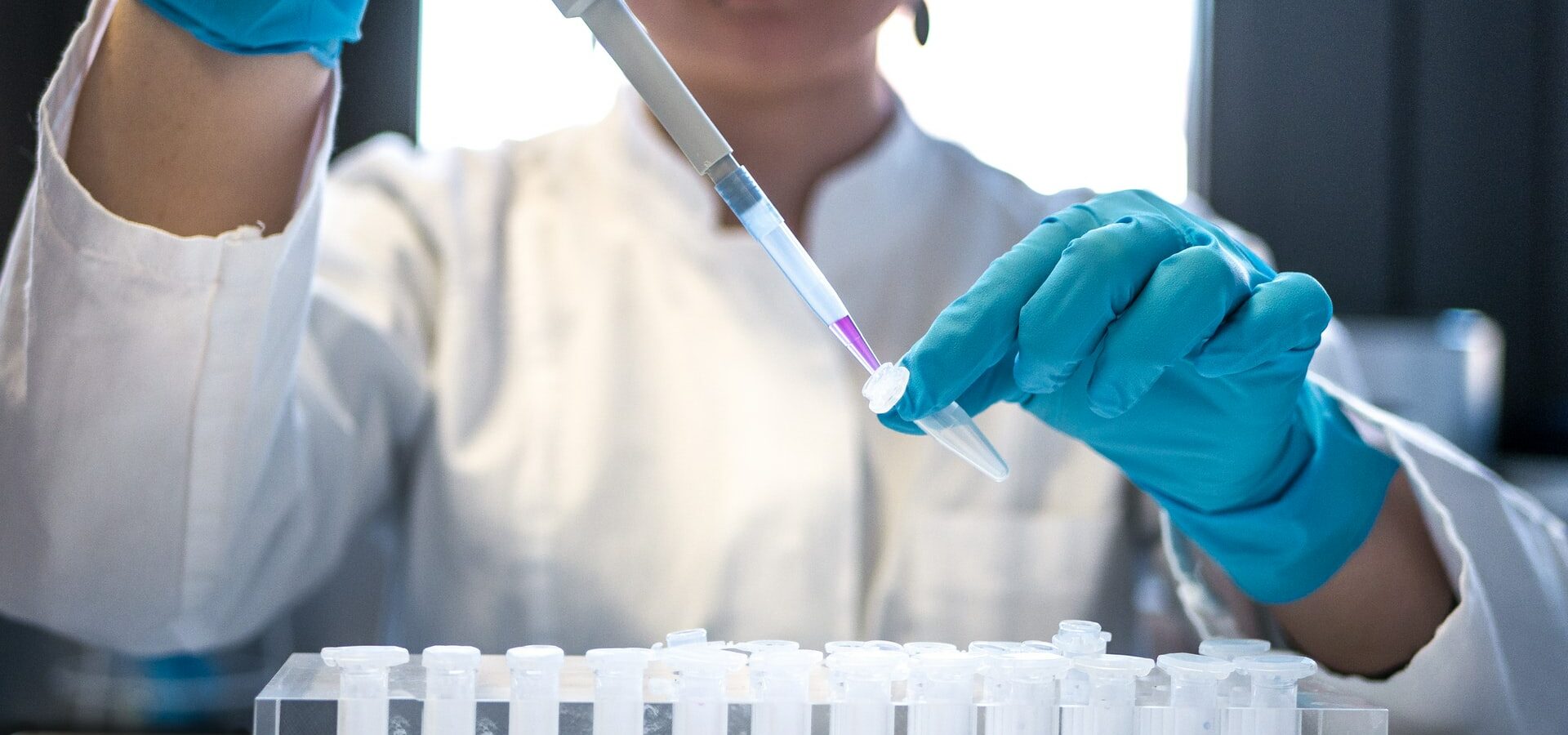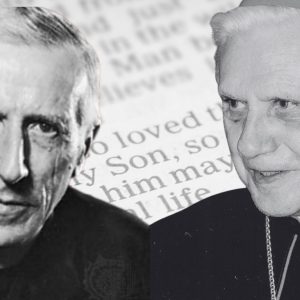“过去两年表明,关于‘科学与信仰的对立’ 的辩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论题,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荒谬对峙”,专栏作家蒂什∙哈里森∙沃伦(Tish Harrison Warren)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1]。这是她从一项调查结果中得出的结论。该调查表明: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是新冠疫苗接种率最低的群体之一。这似乎意味着,在该团体中存在的对科学的怀疑不仅转化为对疫苗的猜忌,而且有意识地提出必须在科学和信仰之间做出选择的要求。
难道对科学的信任与宗教信仰互不相容吗?实际上,这种两相对立的观点揭示的不仅是对疫苗的怀疑,而是一种对科学本身及其作用的错误认识。这种曲解不仅普遍存在于对科学持怀疑态度的人当中,而且或许更危险的是,它在那些轻易拥抱科学的人中也同样常见。当科学无法提供较高的可靠性时,它的失败会引起更大的怀疑。例如,如果将接受疫苗过于紧密地与科学相联,结果可能会使因社会或政治起因而造成的对疫苗的猜忌转化为对科学本身的更大狐疑。
当意识到这种曲解的可能性时,我们从中认识到的影响有助于反思捍卫科学的方式,例如我们对使用疫苗的支持。但是,这些影响也可能提醒我们更慎重地看待一种诱惑,就是使科学或信仰成为对抗我们对不确定性这一人生基本恐惧的堡垒。
相信科学?
在抗击新冠大流行病中,各种确凿的科学证据为接种疫苗提供了依据。因此,那些有所认识并将这种普遍预防措施视为击败大流行病唯一途径的人不断发出 “相信科学” 的呼吁。这种说法听起来不乏吸引力,主要原因是由于科学自启蒙运动以来便已赢得社会的信任,被视为获取真理的途径。但是,我们身边的事实却表明,这个口号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相当数量的各界人士坚持拒绝接种疫苗,其中包括上文中提到的许多福音派基督徒。
笔者现任梵蒂冈天文台负责人:我既是一名科学家,也是天主教会的一员。我对科学和教会当局以及对两者均持审视态度的人,有同样的了解。那种将科学家视为一种保卫真理的司祭的看法值得商榷,特别是在一个真正的司祭也受到怀疑的社会中更是如此。虽然我完全赞成接种疫苗,但 “相信科学” 这一格言令我深感困惑。它所体现的科学观虽然盛行,却易将人引入歧途,也同时有损于科学本身。
“相信科学” 不仅提出科学是通往真理的可靠向导的观念,而且暗示它是唯一可靠的向导。这一表述似乎是在回答一个隐藏着的问题:我们应该相信什么,相信谁?它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若6:68中伯多禄对耶稣的提问:“主!……我们去投奔谁呢?” 也许像福音派基督徒一样熟悉这段经文但对科学缺乏了解的人会意识到圣经的回声,并因此认为这些话暗示着以 “相信科学” 来代替对主的信仰。对这样的人来说,这个口号可能会出乎意料地起到得不偿失的作用。
更糟糕的是,认为科学是唯一可靠向导意味着赋予它战无不胜的权威。但是,所有真正认识科学的人都知道,事实情况远非如此。的确,疫苗能够预防绝大多数接种者染病,并在 “突破性感染” 的情况下减轻疾病的严重程度,但它并非尽善尽美。事实上,尽管已接种疫苗的人很少患有重症,但他们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情况仍然会发生。对于那些反对疫苗的人来说,这种失败不仅表明疫苗并不完美,而且使他们更害怕盲目相信科学可能带来的危险。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但这种对无条件信任科学的恐惧含有合理的因素:科学有时可能制造谬以千里的错误。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可以列举自己以往的科技文章中出现的许多令人尴尬的谬误。并且,在偶然性的错误之外,科学最显著的进步总是伴随着各种错误,包括最终不得不纠正的根本性错误、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假设、必须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的结论,等等。伽利略的地球运动理论是正确的,但他用以支持这一理论的论证却远远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完全错误的,比如基于潮汐运动的结论;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在提出他卓越的电磁场理论时声称,电磁波由一种可压缩的 “以太” 携带,但最终,他的一个工作结果表明,这种以太实际上并不存在;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是对冲击波进行数学描述的创作者,使我们理解了 “超音速” 运动和 “马赫数” ,他采纳了麦克斯韦关于场的观点,并将其作为排除原子的新物质理论的基础:现在我们知道,原子存在是真实的,而马赫的理论则不然;另外,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观察到的星系运动使 “大爆炸 ”宇宙论得到确认,但他本人却从未接受这种宇宙论。
医学和医生向来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批准新药所能带来的财政刺激有可能扰乱为保障安全而设立的严格监管体系。例如,仍有成千上万的成年人至今仍遭受沙利度胺造成的先天发育缺陷: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药物曾经被视为治疗晨吐的万全之策,因此被开给孕妇服用。
同样,疫苗的历史也并非尽如人意。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针对新冠的疫苗会发生偶然性的 “突破性感染”。疫苗接种过程中的副作用是常见现象,其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在批准推广使用疫苗之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是两个需要长期研究的方面;然而,即使在经过这个漫长的过程之后,失误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反疫苗团体最担心的事情并非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情况,可能会真的发生。
但是,最重要的是,历史证明,有时科学——或者至少是向公众展示的方式——不仅被证明是不完美的,而且荒诞不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包括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在内的一些科学普及者以及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等法律专家都是优生学理念的维护者。他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清除 “劣等” 人口而使人类趋于完美。对于他们来说,这一想法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任何以道德伦理理由反对它的人——比如教会——都被其视为一种危险的倒退。
让我们回顾进入流行文学以及电影《风的传人》(Inherit the Wind)的斯科普斯案:高中生物教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因讲授进化论而被带上法庭。可是,所有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都忽略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斯科普斯使用的进化论教科书中有支持优生学的一处,因为它认为进化论 “解释” 了某些种族和民族的 “自然优势”。基于优生学的逻辑,由于波兰人和意大利人被视为劣等人,1924年美国国会的一项法律对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规定了严格的数字配额;另外,此项法令禁止来自亚洲的一切移民。该法律以压倒性多数票获得通过。因此,自1924年起,前往美国的意大利移民锐减了90%。
据估计,美国民众在20世纪中对优生学的认可导致7万名妇女接受强制绝育,她们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这些节育方案的实行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显然,隐藏于纳粹死亡集中营背后的逻辑也正是优生学。
既然科学普及竟会达到如此荒谬的程度,那么从逻辑上讲,是否绝不应该相信科学?当然不是!首先,科学本应站在正确的一边:事实上,在强制性绝育政策终于被废除的几十年之前,优生学便早已广受科学界的质疑。而且,即便是得到科学的支持,它依然是违反道德的。那种推任于 “罪恶的” 科普工作者的做法只会助长过于简单化科学的看法。同时,无论如何,这也无法为那些造成最初失误的科学家提供辩护。
无误性和权威
这个问题具有深刻的含义。实际上,关于 “相信科学” 的争论通常涉及权威的可靠性。毕竟,无论是颂扬科学的人还是贬抑科学的人,他们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宇宙中追求确定性。只是,他们对错误秉持一种近似于加尔文主义的不容忍态度,只想看到一个黑白分明而不愿考虑失误的世界。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学的基础实际上正是怀疑和失误……以及学会分析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不知道的事物;正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这一事实督促我们不断努力探索,而不是满足于已获取的知识。在科学领域,失败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要条件。
科学的不完善性不是偶然的:就其本质而言,它总是不完善的。每当一项进行得好的科学活动在某一领域内取得进展之后,这项工作便已然过时。真正科学进步的标志是推进和提高各领域内原有的理解程度;一旦科学知识取得进展,使其得以实现的工作本身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科学的任务是不断地破旧立新。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哲学或神学截然不同:你可以通过阅读你祖父有关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笔记来学习哲学,但你不会将祖父曾经用过的教科书拿来学习生物学。
当然,对失误保持开放态度的必要性是一个不只限于科学界的教训。仅举一个平凡的例子: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就读期间,我曾经是帆船队队员。在查尔斯河上的无数次航行中,我从未翻过船,但也从来没有在帆船比赛中获奖。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我从未把自己的小船推到最大程度,试探它在翻船之前能够达到的距离和速度。
学会犯错误是一件难事。你必须在以下两者间斟酌一个难以达到的平衡并做出选择:是继续努力一把,追随一个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观点;还是适可而止,承认错误,寻找另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埃德温∙哈勃曾坚决反对宇宙膨胀的观点:但是他错了。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否认了马赫引人瞩目且广受赞赏的新见解,继续捍卫传统的物质原子理论:事实证明,玻尔兹曼是正确的。可见,“新” 与正确和谬误之间并无必然关联。但是,正如在扑克牌游戏中何时、何时弃牌的决定:任何玩家都知道,没有任何计算方法可以代替你自己。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比如通过更多的数据搜集。也许你头脑中的主意要求你彻底改变对已有数据的解释方式。无论对自然界发生的事情提供如何准确的描述,科学都不仅是一种描述而已:它也是对事情发生方式的原因的调查。就其本身而言,科学的目标既不是能够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也不是获取准确的答案:它充其量不过是衡量我们目前的理解水平的准确性的一种方式。
现在,让我们对照一下托勒密和开普勒用来计算行星轨道的不同方法。托勒密系统由圆中有圆的圆组成。从理论上讲,只要在计算中加入足够数量的圆,他就能确定任何可能的行星路径。另一方面,开普勒的椭圆本身并无法解释轻微的行星扰动,因此也并非完全正确。但是托勒密的计算并没有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行星为何以这样的方式运动的本质;事实上,值得怀疑的是,这位科学家本人是否确实提出过这个疑问。然而,开普勒的椭圆却帮助牛顿提出了他的引力定律。
只有当你能够面对原认为已经理解的东西却能够提出:“这是不对的!” 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位科学家。除非你能做到这一点,否则你将不知道从何下手检查失误。然而,遗憾的是,这并非我们传授科学的方式。至少在入门课程中,取得科学试验成功意味着给出与教科书底部相同的答案。但是,在完成入门课程之后,继续前行的人又有多少?让学生死记硬背地记忆习题很可能是激起他们给出正确答案时的感受的最快捷方式。同样道理,在学会演奏乐曲之前必须先练习弹奏音阶。但是,音阶毕竟不是音乐,正如获取答案不等于搞科学。
然而,接受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必须大胆尝试不确定事物所涉及的风险。如果不敢冒翻船的危险,你也就不会在船赛中取胜。但翻船的确是一个既不开心又不容低估的风险。
怀疑与信仰
在信仰中,怀疑具有同样的作用。深受大众欢迎的宗教作家安妮∙拉莫特(Anne Lamott)在Plan B: Further Thoughts on Faith(《备份计划:对信仰的深入思索》)中指出,“信仰的反面不是怀疑,而是确定”。没有怀疑,我们也就不会需要信仰。但是,就像在科学中一样,怀疑是激励我们不断追寻天主的基本动力,而不是满足于接受或拒绝自己在儿童时期学到的东西。保禄∙蒂利希(Paul Tillich)在《信仰的动力》(Dinamica della fede)中写道:“每一个信仰行为中隐含的怀疑,既不是方法论的怀疑,也不是怀疑论的怀疑。它是伴随着每一个风险的怀疑。这不是科学家的永久怀疑,也不是怀疑论者的短暂怀疑,而是热衷于具体内容之人的怀疑,可谓存在性怀疑。[…]它不拒绝具体的真理,但也不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一个存在性真理中都含有不确定因素”[2]。蒂利希还指出:“严肃的怀疑是对信仰的确认。它标志着关注的严肃性和无条件性”[3]。
接受怀疑,担负错误的不可避免性,这也意味着在他人犯错误的时候,对他们抱持宽容态度。我仍然喜欢威尔斯(Wells)的故事,依旧钦佩霍姆斯(Holmes)作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所作所为,还会使用贝尔的电话:虽然他们关于优生学的观点令我反感。我接受英雄有时会是罪人,以至大罪人的可能。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
宗教并不提供某种保证救赎的形式。这种形式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赢得救赎,而不是将救赎作为我们不应得的、来自慈爱天主的礼物来接受。但是,宗教可以向我们揭示我们所得到的礼物,并教给我们一种表达接受的方式。
科学并不能揭示绝对正确的真理。更加精细的实验或理论可能会对自然界作出越来越精确的描述,但每个理工科学生都必须谨记的一个基本教导是需要分清 “准确性” 和 “精密度” 之间的差距。再精密的测量也有可能存在不容忽视的系统性误差。无论我们的科学多么发达,它总是不仅受制于仪器的系统误差,而且还受制于人类强迫数据符合自己先入之见的倾向。任何自认为完美的理解都是死的,它永远不会力求更深的认识。
然而,科学不仅能够对如何看待和认识真理提供帮助,而且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的特定表述的成功概率。我们对疫苗的信任并非由于其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可以大大降低患病几率。真正的问题其实很显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概率的运作原理,正因如此,赌场和彩票行业才总是如火如荼。
当我们认识到怀疑在科学和信仰中所具有的基本功能时,我们将会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当不确定性在两者中的作用被忽略时,科学和宗教才会显得互不相容。正是在两者均被视为不可触碰的规则法典或一成不变的文本的时候,它们才会要求坚不可摧的可信度。但是,确定性并非宗教,而是狂热主义;它也不是科学,而是科学主义。
怀疑论和诺斯替主义
伽利略是一位代表现代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名副其实的英雄。他在其科学哲学论文《试验者》中提出的一个著名原则是:实际观察和实验结果的价值高于一切古老智慧的权威性声明。约翰∙海尔布隆(John L. Heilbron)在为他撰写的传记中略带一丝调侃地问道,为什么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对权威如此不恭呢?他的回答是,这是因为伽利略的父亲和老师的权威:他敢于反叛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是因为他们教导他这样做。
对权威的反叛是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这是出于他们测探自己的自主权极限并对其进行定位的意愿。我想起自己年轻时经常看到T恤衫上印有的一句口号:“反对权威!”。对此,我不由自主地反问:“这是谁说的?”。
某些反对疫苗的人面临的另一个陷阱是:这些人在宣称自己不会愚蠢到甘愿被专家愚弄之后,甚至会采用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完全不宜的危险药物开始进行自我治疗。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竟然把自己的生命安危交托给互联网上建议的药物呢?我们又为何拒绝宗教,而去追随从T恤衫上读到的某一哲学观点呢?
在西方社会中,对权威的反叛与上述对确定性的渴望齐头并进,但这显然是两种相悖的感受:人们无法在要求一个完美真理的同时拒绝任何宣称引导我们走向这个真理的人。这样做的结果是拒绝 “经官方认可的” 权威,却欣然接受由极少数专家所提供的来路不明的知识。
尽管在网页上发现的想法可以被互联网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人信手拈来,但每个人在自己的个人电脑上、在家庭环境中发现它的经历会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它是一种隐秘的发现。这种无声的特性赋予它一种比通过公共媒体了解的信息更高的价值:我们必须注意识别这种诱惑。它具有 “诺斯替主义” 的魅力,渴望接受 “秘密知识”。这种渴求从第二和第三世纪的教父时代便已存在,从古希腊神秘的伊路西尼仪式时代就已经出现,最终,它是伊甸园中蛇的诱惑。
即使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种对秘密知识渴望的表现。科学家——包括本人在内——和技术人员尤其容易自认为世界上的智力佼佼者。由于精通专业,他们丰富的经验有时会转化为一种优越感并延伸到所有的学科。我们从剑桥大学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对天主和宇宙起源进行哲学思考的方式中观察到,他在强调自己并非一个哲学家的同时似乎在暗示: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比单纯的哲学家具有更高的天分。同样,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 Grasse Tyson)似乎对所有人类知识均抱有自己的观念,无论讨论话题与他的专业领域之间存在多么大的距离,他都难以抑制在社交媒体上直抒胸臆的需求。
相形之下,技术人员甚至比科学家更容易表现出这种优越感。科学家对自身价值的感知来自于他们的观点被同事接受和引用的程度,因此对其他人——至少是其他科学家——对他们的看法很敏感,而技术人员的价值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成果。因此,技术人员通常会不顾社会压力地相信某些被所有人视为荒谬的观念,为此,他们更易于成为现代式诺斯替主义宣扬者的猎物。
此外,技术人员的上司往往习惯于在工作中自认为 “房间里最精明的人” [4]。他们所坚信的某些奇思异想似乎难于得到他人的认可,但这一事实不仅不会使他们感到惊讶,反而成为确认自己比其他人更精明的证据。的确,倘若与其他人一般见识,他们怎么可能是房间里最精明的人呢?
如果某些人因为对并不重要的信念进行辩护而丧失某些宝贵的东西时,就会引发一种特别危险的连锁反应,损及其社会地位或者使他们失去工作。这种情况不仅会被视为迫害,而且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使一个非正统的信念陡然变为个人身份的支柱。当你为自己的信念付出高昂的个人代价时,你就会继续固执己见:为接受另一个更大众化的信念而改弦更张将无异于对自己的背叛。
虽然这种倾向在技术人员身上可能表现尤为突出,但并不为他们所独有,而是一种在西方社会随处可见的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再次表明,我们西方人从自己的文化中学到保护个人身份的愿望,却转而以反目成仇的态度回报它。例如,当一位著名运动员表示他将 “通过自己的研究” 来确定新冠疫苗是否有效时,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这一点。在大部分情况下,此类运动员还会一口回绝关于如何提高其运动技能的建议,即使提供这些建议的可能正是他所在领域的专家(比如自己的教练)。这种态度可以增进他的 “明星感”,加强他相对于房间里其他人的优越感。
知识、价值和爱
与其追咎于那些受这种冲动支配的人,也许反思一下此类思想的起因会对我们更为有益。如果假设对科学家以及 “秘密” 网站作者的追随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精明,那么我们就隐约地将 “更精明” 等同于 “更好”。这是诺斯替主义诱惑的根源,自信的感觉来自于自认为比一般人更精明的想法,因为自己才是 “房间里最精明的人”。
然而,这种评估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略的隐含因素:自作精明是个人优越感的表现。这一准则与基督信仰相对立。在玛窦福音11:25中,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而保禄在格前1:17-2:7中强调,福音的智慧与今世的智慧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公认的圣人和英雄人物。19世纪的比利时和法国虽然不乏学识渊博的神学家,但他们通常是势不两立的劲敌,那个时代的圣人却是像伯尔纳德和里修的小德兰一样的人物。
本人无意贬低神学或智力:毕竟,笔者是一位专业天文学家。但是,智力不能与 “价值” 相提并论。在这个方面,我与我的天文学家同事的经验再次向我提供了验证。
无论我们拥有怎样的智力、教育程度和智慧,它们本身并非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只有当它是对我们的造物主的一种赞美时才有价值。我们的一切才能都是天主的恩赐:当我们发挥它们的作用的时候,我们会努力完成我们的使命,从而以各自的方式更圆满地与天主相遇。对我来说,使我认识天主的土壤是天文学;同样,其他人可以在我无法到达的地方找到祂。因此,我们可以在所有的事物中找到天主,在一切事上愈显主荣。
总结
“相信科学” 的说法并不能说服那些最需要被说服的人,特别是当它加重科学正在挑战宗教信仰权威这一恐惑的情况下。此外,如果将科学视为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途径,忽略失败是它取得进步的一个基本要素这一事实,那么科学的失误则只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怀疑。当对确定性的渴望超出科学所能保障的限度时,它会与提倡怀疑权威的文化产生摩擦,对秘密知识的诺斯底式渴望将可能取代权威应享有的赞同。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对以前袭击我们社会的艾滋病毒大流行作出的回应。该病毒的传播通常与性行为有关,因此, “实行安全性行为” 一度成为预防艾滋病的口号。如同 “相信科学” 以及一切口号,虽然它们的逻辑依据就疾病本身而言不无道理,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仅以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性行为并非艾滋病传播的唯一途径。此外,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口号倾向于将性关系的性质简化为单纯的疾病传播渠道,而忽略相关的心理和情感脆弱性:实际上,它们才是性行为的主要因素。疾病并不是伴随性行为的唯一风险。
就其本身而言,性是一种爱的行为,而爱从来都不是安全的。事实上,不安全是正常的。爱上另一个人意味着让自己遭受被拒绝和不忠的风险。但如果没有这种风险,爱的行为也将毫无意义。耶稣本人便是一个典范,他展示了真正的爱的方式,也向我们表明,爱使我们面临背叛的危险。
无论是天文学还是医学,探索宇宙的努力只有当它是对爱的回应时才有可能成功。从事科学的基础是对枯燥乏味的艰苦研究的爱:它要求我们在对科学进步的信心产生动摇时坚定不移;要求我们宽以待人,善于从前人的失误中吸取教训。爱意味着生活于不确定性中,学会相互信任。
但是,我们如何在疾病的不确定性、科学的可错性、丧失个人自主权的不安中生活?这一切都与对他人工作的信任程度相关联。我们一如既往地对我们的人类伙伴给予的爱作出反应:有时谨慎,有时大胆。当我们与爱的机会相遇时,我们知道这种爱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挫折;事实上,我们也不会总是拥有爱的能力,因为我们都是脆弱的人。然而我们知道,不完美的爱仍然远远胜过缺少爱的生活。
然而,我们也知道如何采取理智的预防措施。我们不拒绝爱,但也不会盲目地坠入其中。即使在品味恪守一夫一妻制关系的特殊爱情时,我们仍旧继续依靠由朋友和家人组成的团体,包括我们的教会,他们将在我们的基本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刻及时向我们提供支持。为此,我们在朋友和家人面前互发婚姻誓言的公开仪式极为重要。与此同时,我们还认识到,危机时刻往往可以转化为迈向更深、更完美的爱的步骤。
同样,我们知道,相信科学意味着将我们的信任寄于美丽但可错的智慧中。对于任何单独提出的碎片式 “科学”(包括我们在互联网或其他地方的发现),我们都不能给予完全的无条件信任。我们接受疫苗,是的,但我们也注意保持社交距离和适当的卫生习惯,佩戴口罩。
作为原罪的后果,人类易犯错误的现实既是恐惧的原因,也是喜乐的机会。我们欣喜地看到,尽管科学有种种不足之处,但它增加了我们健康生活的机会。我们感到欣慰,因为天主赋予我们的能力使我们借助于科学,以更深的方式理解和欣赏祂的创造。我们欢悦,因为再大的挑战和诱惑也无法阻挡爱的凯旋。而这个操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教会中存在的同样动态。圣神可以在其中引导我们,但作为不完美的人,我们通常不顺从祂的引导。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随着每一次成功,人们认识到天主可以通过我们工作。正因为没有任何成功是确定的,所以我们会为取得每一个成功而感到荣耀。最终,生命中唯一确定的事情是天主的爱和怜悯,以及我们对它们的需求。
-
T. H. Warren, «How Covid Raised the Stakes of the War Between Faith and Science», in New York Times, 7 novembre 2021. ↑
-
P. Tillich, Dinamica della fede. Religione e morale, Roma, Astrolabio – Ubaldini, 1967, 29. ↑
-
同上,第30页。 ↑
-
参见B. McLean – P. Elkind, 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