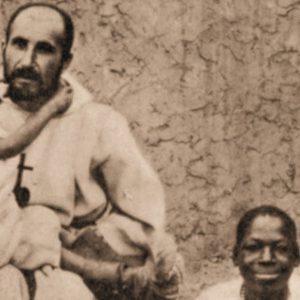复杂性的悖论
尽管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选项,但生活似乎并没有越发容易。这就是所谓的“复杂性的悖论”(paradosso della complessità):我们研发的系统本应让生活更轻松,但与此同时,进步也要求学习新技能,有时这些技能极其复杂,以至于衍生出新型文盲[1]。换言之,机会的增加并不一定让生活变得更轻松。事实上,某些研究已经表明,一部分人宁愿较少的选项,以避免因错误选择而引发的恐惧[2]。
因此,幸福并不意味着总有新的机会或多样的产品和优惠。其实,复杂还会让人触及更大的痛苦:在购得一件产品后,我们有时会质疑,这是否算得上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的可能。
市场的复杂性改变我们感知现实和适应现实的方式。例如,它让我们更敏感于细节,有时甚至是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和差异;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加挑剔,在比对两样产品时吹毛求疵;市场的复杂性让人对不同的观点变得激进好斗,这往往会造成一种强烈的两极分化、一种防御机制,这也反映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我们将自己置于张力的一端,以避免做出选择。
对复杂性最常见的反应之一就是试图将所有品质放在一起:最受欢迎的产品因此变成了包罗万象的产品,也就是说,能让我们在没有任何割舍的情况下,鱼和熊掌兼得。这就是复杂性时代的效率神话。不幸的是,这种理想式诉求也被虚幻地延伸到人际关系中:例如,我们妄想自己的伴侣能拥有我们所想要的一切品质。因为“鱼和熊掌兼得”的情况亘古未有,后现代人便通过频繁更换伴侣来解决这个问题,乌托邦式地寻求那并不存在的理想。当我们试图将不适合一个人—要么限于年龄,要么限于生活处境—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融于一身时,我们也会将兼容并蓄的神话投射到自己身上。我们希望在没有任何割舍的情况下应有尽有。
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因为我们的选择都是偶然而不可逆的[3]。确实,一个选择有时会被后续的另一个选择纠正,但事实上,在历史中发生过的最初的选择是无法抹去的,始终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我们不可能忽视它,就像一个无法被抹去的纹身。
你所做的和你所成为的人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商业领域,层出不穷的出版物试图解释怎样才能做出一个决策;其实,借用西方的实用语言,这里所说的就是“做决定”(decision making)[4]。这些理论中确实有一些有趣的要点,但主要的局限是忽略了主体,而主体在做选择时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以至于他通过决策建立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我们想要在本文强调的重点。
“做决定”的过程通常使用树状结构:我们从那个表示起始情况的点开始,然后通过构成树的分支的替代方案循序渐进,直到达成了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不同的分支都是从中转节点处脱颖而出,这些节点代表了朝着目标循序渐进的每个决策的关键步骤。每个中转节点都通往一个可能的世界,但只有其中的一个世界会因人的涉足而变成现实。鉴于此,若不经过中转节点,就不可能从一个世界转向另一个世界,这个中转节点实际上代表了人生中一个让我有更多可能选项的契机。
显然,在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转换中,主体本人正在书写着历史,不仅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中,而且也在别人的生命中。例如,若马里奥决定不与朱莉娅结婚,那么,这个决定不仅会在他的生命中留下痕迹,也包括朱莉娅的生命中,因为朱莉娅不会嫁给马里奥。这不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观察,因为它开始让我们思考:我们的选择所附带的责任绝不只关乎到做决定的当事人。这也是已故教宗方济各一再强调的相互关联(interconnessione)[5]。
相互关联,责任和自欺欺人
从理论的角度,决策过程中出现的相互关联可以根据博弈论重新解读,博弈论的奠基人首推诺伊曼(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6]。一开始,博弈论只是为了解在扑克牌游戏中如何使用偷鸡(Bluff):你必须从中找到平衡,使诈不到位的话,可能会冒着输掉的风险,相反,太过于虚张声势就会被发现。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很好地描述了我们的决策不仅对我们自己有影响而且也会涉及他人:两名重犯嫌疑人被捕,但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们。为了让他们认罪,警方想出一个策略。两名嫌犯被分开审讯,如此一来,二人无法彼此交流。两人都面临几种情况:1)如果两人都不招供,将从轻发落,判处六个月监禁; 2)若其中一人坦白,另一人拒不认罪,前者将无罪释放,后者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3)若两人都坦白,那么两人都会被判刑,但会减刑。
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决定总是受到不知他人如何选择的影响。通常我们会预设对方采取自私的做法,这会不利于我们。在囚徒困境中,最常见的后果是,两名嫌犯都会选择认罪,从而排除了第一种情况,虽然这个选择最合算,但需要对同犯有着心有灵犀的信任。
博弈论可被视为是我们生命中许多决策过程的隐喻。另一方面,在这些决策过程的理论中,我们一如既往地发现:人们的兴趣集中在选择的后果,而不是主体本人,通常情况下,决策过程会潜移默化地帮助决策者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文学作品也描述了我们的决策过程具有的相互作用和后果。例如,萨特(Sartre)在他的戏剧《闭门》中意在强调不幸的处境,我们因为害怕未知而决定让自己置身其中,也就是说,此害怕源于一种可能发生的变化,而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结果[7]。这就是“自欺欺人”的概念。
该剧的主角名叫加尔辛(Garcin),他背叛了妻子,甚至强迫妻子为他和情妇提供床上早餐,最终落入地狱。加尔辛去世后,他的妻子也自杀身亡。来到地狱后,加尔辛以为自己会遭受可怕的折磨;相反,他却发现自己和另外两个女人共处一室,与她们的共处成为他苦痛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情景下,那句名言应运而生:“他人即地狱”。加尔辛所处的房间有一扇门,他原以为是关着的,但直到最后才发现这扇门一直开着。于是,加尔辛敲了敲那扇门,希望有人能听到并让他出去。当信使最终出现时,他给了加尔辛一张前往虚空的门票,而不是滞留在房间里。但加尔辛拒绝,他宁愿承受确定的痛苦,也不愿选择未知。
多重选择的困惑
后现代人习惯于掌控和量化,但正如囚徒困境所表明的,抉择始终伴随风险:我们几乎拥有了足够多的关乎我们自己的信息量,但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知道那些捉弄我们之人的真实意图。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选择之所以困难,正因为它暴露了人无法掌控的不确定性,而这恰恰是后现代人倾向于逃避的。凡是想要掌控全局的人往往不做选择或拖延决策。
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这种风险和不完善(incompiutezza)让人感到痛苦。海德格尔称之为Dasein(esserci,当下的存在)的人类会持续不断地面临选择的机会。人的存在实际上如同一个企划。其实,正因为有这项做出抉择的使命在召唤人,所以,唯有当下的存在才真正存在,也就是说,人不受制于生命境况的任意摆布。相反,事物,也就是所有其他的实体,仅仅就只是“在那里”,停留在既有的状态之中。对海德格尔来说,Dasein一词实际上想表达的不只是人类与存在(人之所是)所有的特殊关联,即人能质疑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且还指出另一事实:人持续性地置身于某种境况(正如小品词-ci 所示)。这个小品词-ci是一个起点,生命过程中一个永无止境的状态。
正因为Dasein不断地面临进一步选择的可能,所以它永不安于现状,也没有任何境况被认为是终点。正是这种不安于现状(spaesamento)带来了痛苦[8]。这并非一种消极的感受,而是关乎存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当下存在的生命所特有的,也是将人从其他受造物区别开来的标志。这些事物只不过是“唾手可得的”,而Dasein却将它们纳入其意义范畴,以构建属人的企划[9]。然而,海德格尔指出,选择并不总是真实的:实际上,有时候,Dasein按照属血肉之人(Man)的逻辑进行选择,也就是,普罗大众的“是”(喜好),即受到出于本能的所说、所做的影响。相反,当人选择最相称于人之所是的可能性,即真正属于人的那份,Dasein就过着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换言之,就是一种原始的存在。
尽管Dasein面临的可能性很多,但也不是无限的。幻想有无限的可能,甚至会引起决策拖延症,或者永远也无法在自己的人生企划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总以为这个企划是无限期开放的。例如与最新的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超人类主义(transumanesimo)联系在一起的永生假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让人幻想生命是无限期的延长,这些假设诱导人永远不对人之所是做出抉择。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会终结所有可能性,那就是死亡的来临而死亡随时都可能到来。预见死亡意味着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只有承认自身存在的有限,才能让人对人之所是有真正的认识。预见死亡意味着承认我是我之选择的结果,一旦死亡在某个时刻关闭了我进一步选择的可能,那么,我之所是也就在那个时刻被最终定格。
做决定给予的身份认同
得益于利科(Ricoeur)的反思,我们现在可以尝试通过不可避免的决策过程来理解主体身上发生的事情,而决策者本人的生命秘钥(cifra)就在于不断被要求进行这一决策过程。换句话说,在这项属人的活动过程中,无论意识的感知度多么不同,我们都不可能不做决定。
决策现象学的第一个面向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决策过程宣告了意识孤立状态的终结。利科通过分析贯穿整个决策过程的动词得出了这一结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是及物动词(我觉得、我渴望、我想要……),这些词语反映的是决策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不及物动词和反身动词(我决定、我妥协、我解决……),这个现象凸显了选择会对做决定的人产生影响[10]。
作为一个过程,决定与时间进程有关。首先,因为决定是关乎未来的一个空洞的称谓:它其实指的是一个尚未发生的行为,最终也只会在以后完成的行为,因为其后果目前来说还不真实,只不过是假定的。
尽管着眼于未来,但决策过程却牵涉到当下的努力:无论谁在做选择,都会根据今天的事实畅想来日的情景,而他相信眼下这些想象到的可能都尽在掌握之中。这个做决定的人明知是他本人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将自己当作了赌注。
在决策中浮现的自我认知过程对于承担责任可谓至关重要:在那个行动中我看到了自己;沉浸在思考中的那个“我”与最终将完成想象中的行动的主体是同一个人。蓝图设计者的“我”在项目参与者的“我”中认出自己。举例来说,我会避免杀人,因为当我想象那个情景时,我也意识到我将成为杀人行为的责任人。同样清楚的是,一旦这种自我认知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就会发现自己在采取行动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后果。
从当下的分辨到未来的决策,也适时地经过了犹豫,这是反思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未来的我将会和现在的我不一样。因此,该决定从现在起就是一种透支。这是一种失去,因为我正想象自己不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决定中,我将自己当作了赌注,我抵押了我的形象,我将自己封印在未来。
做决定也开启对未来的积极看法:事实上,我意识到,正因为我可以决定,我才拥有一个可能的未来,而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尚未被定型。与此同时,我也认识到当下的局限性:今天的我是这样的,这也正是我可以开始的地方。这种当下的局限被我的身体以最直接而明确地表达出来,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目前所处的状况。鉴于此,身体被利科称之为“不由自主的地方”(il luogo dell’involontario),因为这是我可以选择出发的起点,但同时也是我无法避免或移除的起点。这也是我别无选择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体有时被描述为一种原始的失败[11]。
欲望和复杂性
身体是关系的纽带,也是我在关系中展现自己的方式,是别人了解我的窗口,也是我得以建立关系的工具。身体不断提醒我在人之为人的架构中那个缺乏的维度。我们总是需要与外界联系,例如养活自己。
这种匮乏在更深层次上呈现出欲望的特征,它不只是残缺的不幸,更是启动决策过程的引擎。当我们感到有需求时会寻找可以填补缺口的东西。这个需求本质上是指身体的必需品。另一方面,欲望虽然具有与需求相同的匮乏特征,但却超越其对象,而且,除非找到张力所致的对象,否则永远不会得到彻底满足。事实上,欲望与我们的价值观有关:我们渴望实现某些目标,因为我们认为它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可以说欲望具有幸福论(eudemonistico)的特征[12]: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在物质层面(基于本性的需求),也在更深层次的价值方面,寻求那些被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欲望是有目的性的,因为它指给我们一个目标,并以此推动我们。亚里士多德用欲望的比喻来解释第一推动者如何在自身不动的情况下吸引天体向其移动[13],这并非巧合。
通过想象力,欲望让我们预见那尚未存在的事物,而这个愿景让我们以最强劲、最饱满的状态行动起来。如果欲望势弱或消失,我们便会安于现状。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追求的生活会让人陷入浑浑噩噩、一潭死水的状态。因此,欲望的觉醒是开启分辨过程的必要条件。这并不意味着欲望是选择的标准,相反,欲望是推动人最终走上决策道路的引擎。
通往决策的道路总是充满迷茫。缺乏清晰度是决策过程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正在构建的东西尚不存在,也从未有过完全相同的先例,以至于我们不可以轻省地复制它。每个选择都是独有且原创的。在选择中面对的是普遍原则和个案的碰撞。一般性或普遍性是参考的标准、价值观和规范:一些普遍性因素源于合理性,而另一些则与做出选择的共同背景相关。然而,这些普遍性的面向必须与偶发情况进行对话,因为后者始终是独特且原创的。分辨的困难恰恰在于将现实的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
决定之所以是复杂的也因为我们经常会面临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例如,我们必须在友谊和正义之间、透明和隐私之间、冲动和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为此,利科认为决定就像是“黑暗大海中的一座明净小岛”[14]。
由于决策是一个要求主体认识自我的过程,因此决策者最终总是会同意。最终决定权在我。同意有时也意味着接受我无法改变的现实:与其说是逆来顺受,倒不如说,我答复了是(fiat),“那就接受吧”!我们无法改变现实,但我们总是可以决定如何生活。
决策过程以行动结束。其结果总是一项切割。在精神分析领域,人们可能会谈到行动的执行:动作被执行。但“执行”一词也指死刑的完成。事实上,做决定也意味着杀死所有其他的妄想,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能,也将所有其他可能性判处死刑。借用一种颇具灵修意味的表达,我们可以指出,“决定”(decidere)一词与“切割”(recidere)具有相同的词根:一旦将剩余的部分全都切割掉了,也就等于真正做出了选择。无论我们偏好哪种表述,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单词都指出选择具有的痛苦维度:就像分娩一样,虽然痛苦但富有成效,。
一个宝贵的契机
从这篇对决策的分析报告来看,首先浮现出来的是主题的实效性,因为它顺应这个以复杂性的悖论为特征的时代。多种的可能并不一定,也不直白地预示着更幸福的生活。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旨在强调主体的作用以及主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自我认知。相对于那些唯独侧重以最佳方式达到目标的观点,这类观点常见于企业领域,
,决策现象学则想要明确决策主体在做决定时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重要的,因为它与个人身份的构建有关。
对选择过程的描述指出我们回避不了做出决定的需要;这种倾向也正是人类的特征。我们不断地被要求做出决定,不仅如此,每个决定明显都带来不同的后果并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因此,原本只能被视作一场灾难的选择性困难却也被证明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做选择的人可以通过它来建构和认识真正的自我。
- Cfr E. C. Rosenthal, The Era of Choice. The Ability to Choos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Life, Cambridge, MA – London, MIT Press, 2005, IX. ↑
- Cfr ivi, 42. ↑
- Cfr ivi, 9. ↑
- Cfr T. Connolly – H. R. Arkes – K. R. Hammond,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Cfr, per esempio, Francesco, Laudato si’, n. 117. ↑
- Cfr J. von Neumann – O. Morgenstern (edd.),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
- Cfr J.-P. SARTRE, Le mosche – Porta chiusa, Milano, Bompiani, 2013. ↑
- Cfr M. Heidegger, Essere e tempo, Milano, Longanesi, 2020, 28-30. ↑
- 译者注:正如上一段刚刚提到“人的存在实际上如同一个企划”,所以,人和物体的不同就在于,人不仅能意识到自身生存之意义,而且能赋予万物意义,即,万物为我所用。这些被赋予意义的事物最终帮助人达成“人之为人”的目的,也就是构建人自我的身份认同。 ↑
- Cfr P. Ricoeur, Filosofia della volontà. 1: Il volontario e l’involontario, Torino, Marietti, 1990, 46. ↑
- Cfr Id., Finitudine e colpa, Bologna, il Mulino, 1970, 227. ↑
- Martha Nussbaum ha esteso il carattere eudemonistico alla sfera delle emozioni nel suo complesso: cfr M. Nussbaum, L’intelligenza delle emozioni, Bologna, il Mulino, 2004, 47. ↑
- Aristotele, Metafisica, XII 1072 a 20 – 1072 b 10. ↑
- P. Ricoeur, Filosofia della volontà. 1: Il volontario e l’involontario, cit., 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