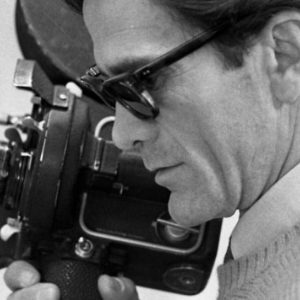导言
郎世宁,本名Giuseppe Castiglione,于1688年出生在米兰的一个名门望族,是清朝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自幼便展露出非凡的绘画天分,曾师从于卡洛·科纳拉(Carlo Cornara),在其门下接受了严格的艺术教育。然而,他所展现的艺术风格主要是受同会弟兄、耶稣会士安德烈亚·波佐(Andrea Pozzo)的影响。波佐是一位巴洛克透视法大师,他在透视错觉天顶画和以错视画法(trompe-l’œil)绘制建筑物方面的创新技巧在郎世宁的作品中得到了共鸣[1]。
1707年1月16日,郎世宁作为一名终身修士进入热那亚耶稣会的初学培育,开始了他毕生将艺术与信仰融于一体的使命。经过初学阶段为期两年紧张的灵修与学识培育之后,他被派往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进一步为传教工作做准备。这一时期不仅增进了他的神学和文化知识,也锤炼了他的艺术技巧,为他在东西方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独特任务做好了准备。
郎世宁于1714年启程来华,于1715年8月20日抵达澳门。在那里,他潜心钻研汉语及中国文化,直至同年12月被康熙皇帝召进皇宫。出众的艺术才华使他迅速赢得青睐并被册封为宫廷画家,接连供职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
郎世宁独特的绘画技法及其对西方写实主义与中国传统审美的融合始终是一个备受学术界研究关注的课题。对此,我们将在本文中采用一种不同的视角:与其局限于对其作品进行纯粹的技术分析,不如对他的某些画作进行探究,以求深入了解这些作品如何反映儒家思想的关键要素。我们将探索郎世宁如何与儒家思想建立联系,并将儒家哲学原则巧妙地融入其视觉叙事和艺术表达之中。
欧式宫苑建筑设计师
在郎世宁为清廷做出的众多贡献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被任命为北京圆明园中的欧式宫苑建筑群西洋楼的总设计师,而圆明园亦以“老夏宫”之名而闻名遐迩。当时的郎世宁已客居中华大地30年有余,而且也已经深愔中国皇室美学、乾隆皇帝的艺术品味以及中国传统山水画复杂的基本理念。在发挥这些渊博知识的同时,他着手于一项将会重新定义清朝宫廷艺术景观的宏图。
他将16世纪末和17世纪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元素大胆地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引入了欧洲美学所特有的充满人文主义、民族主义及宗教精神的设计元素。其设计手法以宏伟、对称和对细节的一丝不苟为特征,而这些特质恰恰迎合了乾隆帝的高雅品味。郎世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几个重要建筑物上,其中包括:
– 远瀛观:一座专为皇家宴饮聚会而设计的宫殿,具有浓厚的欧洲巴洛克风格和华丽的空间布局。
– 海晏堂:著名的大引水渠所在地,这个精心设计的喷泉系统既体现了欧洲水利工程的精细并赢得清廷的青睐,也展示了西方工匠的技术专长。
– 大水法:壮观的中央喷泉,配有精美的大理石雕塑装饰,其中包括著名的十二生肖像。这些雕像不仅体现中国历法和每个人的属相,也是皇帝的天下观以及皇权天经地义的有力象征,在从视觉上重申清朝的统治权威,传递着显示皇家园林的和谐、神圣与威严的信息。
在这些设计中,郎世宁巧妙地将欧洲艺术原则与中国传统建筑和景观美学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中西合璧的风格。同时,他的贡献超越了美学创新,成为一种思想和文化对话的代表,在促使清廷对外国艺术影响保持开放态度的同时又秉持了传统的中国哲学及汉文化精髓。此外,于郎世宁而言,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巧妙地塑造了其艺术生涯,促成了他的作品与其委任者以及当时更广泛的知识环境之间的深刻默契。
艺术作品
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十分着重和谐,主张建立一个天地人和谐共存的和平世界。《礼记》中所描述的儒家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强调个人修行、社会和谐以及以国民正义与福祉为中心的执政风格。这些深深植根于汉文化的原则在郎世宁的作品中得到了其独特的艺术体现。
《百骏图》:艺术传统的交融
1728年,当郎世宁奉雍正皇帝之命创作《百骏图》[3]之际,这位艺术家已经在中国度过了13个春秋,在此期间,他潜心研究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艺术。他对这些哲学理论的理解深刻地影响了其艺术表现,使他将西方现实主义与中国美学进行了创新而和谐的结合。
这幅画的构图以古松为中心,松树在中国文化中是坚韧、正直与长寿的象征。松树之下,三位牧马人正在宁静的乡村氛围中休憩。一匹健壮的白马立于近处,另有许多骏马在青翠的山水间吃草、嬉戏、翻滚,其姿态栩栩如生。对细节的雕琢和对动作的细致处理不仅为画面增添了活力,也使观者得以把握画作里所有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中国传统中,马既是美德的象征,又是君子精神的体现。奔腾的骏马喻示着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安康。郎世宁在画作中央绘制了一片宁静的湖水,湖面如镜,倒映着芦苇、垂柳和青草,营造出一种宁静和谐的氛围。山、水和植物的完美融合–西方透视技术与中国绘画处理明暗的“皴法”的微妙平衡–将这幅画转化为对儒家通过大自然追求内心平和宁静的诗意呈现。画面的结尾是一位只身的牧马人,他的出现巧妙地将观众的视线引向整幅画面,也同时强调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运用西方的明暗对比和三维技法,郎世宁巧妙地以现实主义将群马描绘得栩栩如生;与此同时,他也以中国的传统笔法描绘了崎岖的地形、树木和草叶。此种构图将多个场景天衣无缝地交织于一图–休憩中的牧羊人、徜徉于丛林中以及在河边沐浴或正趟过溪流的骏马–每一个场景都捕捉到骏马的高贵本质,使观者沉浸在人与自然宁静和谐的愿景中。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画作中三匹特别消瘦的马,它们在健壮活泼的马群中显得格外突出。它们憔悴凄凉的身影与同伴的生机勃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令人想起元代诗人马致远《秋思》中令人伤感的诗句:“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4]。
虽然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表明郎世宁明确地以这些瘦马来指代他自己,但我们不禁自问:画家是否也像这匹孤独的骏马一样,感受着未竟之志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他跋涉重洋,只为将福音带入中华大地;然初至京师,便被囿于皇宫深处。虽其艺术造诣令人叹服、广受推崇,然其心中真正神圣的使命,却迟迟未得实现。这种微妙的平行关系呼应了儒家情怀,即因怀才不遇而遗憾的伤感。
尽管《百骏图》的构图错综复杂,但仍保持了精彩的平衡。人物、骏马、风景和花草的精心安排形成了有序的节奏,强调了儒家万物和谐的理念。这幅画展示了一幅以牧马人开篇和收尾的构图场景,在颂扬人类、自然及宇宙之间共生关系的同时,也含蓄地强调了以人为本的观念。
《八骏图》:哲学和艺术的延续
郎世宁的另一部杰出作品《八骏图》[5]同样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这幅作品中,郎世宁巧妙地融合透视及明暗对比等西方技法,不只是为了描绘骏马,也是为了呈现牧马人以及周边的风景。这种东西方艺术传统的结合形成一种生动逼真的表现手法,也同时传递了在《百骏图》中有所表达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理念,即:人类、自然和万物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田园牧歌般的宁静让人不禁沉思儒家对平衡与和平世界的愿景。
与自然景观一样,马也是郎世宁最常见、最具象征意义的题材之一。如前所述,在传统儒家文化中,马代表着美德和道德操守,体现着力量、忠诚和卓越。在中国皇权社会中,马代表着君主对人才和道德的尊重。因此,郎世宁作品中描绘的骏马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们体现帝王识人善用,广招德才兼备之士为国家效力、确保国家繁荣昌盛的期冀。
在郎世宁的艺术作品中,马还暗指中国传统的“龙马精神”,是非凡、活力与胆识的象征。这些马超越其外形,体现着王朝的智慧和道德潜能。在艺术家的笔下,马成为深得帝王赏识的臣民的隐喻,暗示那些在贤明指引下为社会繁荣做出贡献的贤能之士。
这种艺术手法反映了郎世宁对中国哲学和文化观念的深刻理解,为其作品注入了颂扬忠诚、智慧和才能的象征意义。他的画作不仅颂扬了皇帝在表彰杰出人才方面的作用,也展示了郎世宁本人与清朝效忠理念相一致。因此,《八骏图》超越了单纯的图画表现形式,表达了深刻的文化价值观和对德政的肯定。
通过《百骏图》和《八骏图》,郎世宁巧妙地在两个艺术与哲学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其作品不仅彰显了高超的技艺,而且与中国文化和儒家理念有着深刻的契合。这些兼具美感和意义的画作,将西方艺术技巧与中国主题和象征融为一体,彰显了跨文化交融的巨大潜力。通过对马的高贵本质的描绘,郎世宁所呈现的不仅仅限于绚丽的视觉效果,而且也是对美德、和谐以及对理想世界永恒追求的深思。
《嵩献英芝图》和《瑞谷图》
在众多反映儒家思想的作品中,《嵩献英芝图》[6]是一幅寓意深刻的杰作。这幅画将自然元素和丰富的隐喻巧妙地结合于一处,描绘了一棵苍松、一只作为构图焦点的白鹰、一条流淌的小溪、飞溅的水花、嶙峋的岩石和数株灵芝。郎世宁巧妙地运用了绚丽的色彩和精细的造型,使每个元素都显得栩栩如生,但它们在此画中并不仅仅是风景,而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精妙的视觉展示,旨在表达美德、长寿和君权天授合法性等主题。
这幅画是于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为皇帝祝寿而绘制的作品,既是艺术献礼,又是政治宣言。图中的每个造型均经过精心挑选,以强化吉祥寓意:松树向来用以指代坚韧不拔,象征着皇帝坚定不移的力量;白鹰体现敏锐的洞察力、行动的敏捷和高超,反映统治者的智慧和权威;灵芝是一种稀有且非常珍贵的药材,象征着和平、健康和繁荣;巍峨的岩石在风雨面前毫不动摇,代表着稳定和坚韧,同时也是巩固王朝统治的永恒力量。
此外,这幅画的标题还蕴藏着一层更深刻的含义。“嵩献英芝” 与“松”、“鹰”、“芝”的谐音构造了一种微妙而有力的语言游戏,增强了画作的吉祥寓意。对词语的精心选择不仅强化了长寿和吉祥的主题,而且也反映了郎世宁对儒家价值观的深刻理解及其融合西方艺术技巧与中国传统象征意义的能力。因此,《嵩献英芝图》超越了单纯的视觉美感,成为一种对文化思想的精妙表达,体现了对太平盛世的祈愿。
同样,《瑞谷图》[7]是宫廷绘画的另一个典范,体现了丰收、繁荣和儒家重农思想的主题。这幅作品是雍正皇帝在1723年的大丰收后降旨绘制的,它既是对举国农业丰登的庆祝,也是对皇帝德政的歌颂。1727年,雍正皇帝颁示此画,他在谕旨中强调人民福祉在立政中的根本作用曰:“今蒙上天特赐嘉谷,养育百姓……以勤民为立政之基”[8]。
在儒家农耕社会中,农业是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基础,帝王对这一原则的认可堪称至关重要。国家繁荣和人民福祉与土地肥沃和五谷丰登密切相关。因此,君主的角色不仅是政治领袖,也是瑞谷嘉禾的守护者,肩负着实现天、地、人和谐共生之重任。
《瑞谷图》所呈现的繁荣景象直观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既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对皇帝以智慧和正义进行统治的象征性肯定。这幅画上绘有五株稻穗,它们寓意不同但密切相关,象征着国泰、民安、家和、业顺和人兴。这些寓意反映了儒家关于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理念。除了其美学和象征意义之外,此画作亦是丰收年景的历史见证,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一位以德治国、仁爱为怀的帝王必将得到丰收的回报。这是一种对“天命”观念的强调,即只有保持天命、恪守正道的统治者,方能确保帝国的繁荣与安定。《瑞谷图》的艺术表现形式不仅是对农业丰收的纪念,也强化了皇权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对君权神授的认可。
通过这些作品,郎世宁超越了宫廷画家的角色,成为一位文化价值观的诠释者,将西方艺术与儒家哲学完美地融合起来,而这种将不同传统融汇在一起的能力使其画作不仅在视觉上精美绝伦,而且也具有丰富的思想和道德内涵。郎世宁以此巩固了自己作为文化使者的地位,他的艺术至今仍令人迷恋,给人以启迪。
《聚瑞图》
郎世宁于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绘制了《聚瑞图》[9],以纪念雍正皇帝登基,并庆祝其统治初期所取得的政绩。画家在这幅画的右上角写下了这样的款题:“皇上御极元年,符瑞叠呈,分歧合颖之谷实于原野,同心并蒂之莲开于禁池。臣郎世宁拜观之下,谨汇写瓶花,以记祥应。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海西臣郎世宁恭画”[10]。
郎世宁以两个自然植物–瑞谷和并蒂莲花–来表达国家繁荣、稳定和仁政的主题。画中绘有一茎双穗瑞谷,用以象征国家的繁荣富强和多元化发展。这一形象不仅是对皇帝德治之下太平盛世的体现,而且也代表着对人民祥瑞临门、安居乐业以及对皇帝作为统治者以廉治国、盛世承平的祝福。
此外,并蒂莲进一步增强了象征意义的深度。在中国文化中,莲花代表着纯洁、坚贞和吉祥,而一茎双花更是具有双重祝福与和谐繁荣的寓意。莲蓬中的莲子象征着多子多孙,强化了王朝延续和皇权稳定的主题。此外,莲叶即使在浑浊的塘水中也能纤尘不染,巧妙地暗喻着皇帝的道德操守和对秉公治国的承诺。
除了代表富贵昌盛和社会和谐之外,《聚瑞图》还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在构图中,这些吉祥元素被精心安排在一个花瓶中,象征着国家的稳定与和谐。这种对意象的精心设计体现了儒家的原则,即德政是太平盛世的根基。
纵观历史,中国历代皇帝将天命视为其合法性的终极根据,相信上天会眷顾那些保持道德操守且怀保万民的统治者。因此,郎世宁画作中所描绘的吉祥瑞物被视为皇帝德操及其统治稳定的具体见证。通过亲笔描绘并明确展示这些象征吉祥的瑞物,郎世宁增强了所描绘符号的可信度,并进一步强调了它们的象征意义。
通过艺术语言,郎世宁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体现了文化融合的精神。
此外,艺术家可能在这幅作品中加入了一个微妙的外交暗示,希望雍正皇帝能像他的前任康熙皇帝一样对传教士保持宽容态度。通过创作一幅符合中国文化和哲学观念的画作,郎世宁希望遵循耶稣会传教士在清廷使用的外交策略,赢得皇帝的垂青。他将儒家价值观和帝王象征符号融入艺术的能力不仅体现了其艺术造诣,也体现了他对清朝政治和文化格局的深刻认识。
总而言之,《聚瑞图》不仅仅是一幅简单的花卉画:它是融艺术、政治及儒家思想于一体的精妙见证,既反映了雍正统治的强大,也象征着中华帝国文化的持久生命力。
结语
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的重要灵修原则之一是“在万事万物中发现天主”,在存在的各个方面认识到天主的临在。这一原则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一种生活体验,一种为日常生活注入使命感和神圣感的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作为一名耶稣会士,郎世宁将依纳爵灵修带到了中国,并在那里为服务于清廷而奉献出生命中的愈五十个年华。虽然无法按照自己的初衷直接从事福传工作,但他却发现了一种传教的替代方式,一种超越语言和教义的方式。通过艺术语言,他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以此展现了耶稣会士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所致力的本土化精神。
郎世宁将透视、解剖和明暗对比等西方艺术技巧与中国水墨画的美学和哲学传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独特而创新的宫廷绘画风格。他的作品不是单纯的皇室视觉图像记录或宫廷装饰品,而是充满了多层面文化象征、儒家思想以及对艺术和灵性真理的深厚敬意的创作。在他细腻的笔触中,人们发现了两种伟大文明的融合,这两种文明分别以各自的方式感知美、秩序以及人类与宇宙之间的联系。
郎世宁的作品不仅是其艺术造诣的见证,而且也反映了一种深沉的灵性探索,一种对天与地、传统与创新、可见与超越之间和谐的追求。他的画作呼应了皇权、自然丰饶和万物相互联系的主题,体现了儒家的秩序观,同时也巧妙地揭示了耶稣会士在万事万物中发现天主的追求。通过他的画笔,信仰与文化浑然一体,创造了一种艺术遗产流芳百世、给人以启迪的生命力。
他的贡献不仅丰富了中国绘画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宫廷艺术家,而且也在更广泛的东西方艺术和思想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郎世宁的作品中,我们目睹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刻:艺术超越了媒介,升华成为文化对话的形式、理解的工具和跨文明的桥梁。郎世宁不仅是一位为皇帝效忠的画家,更是一位有信仰的人,其使命恰恰体现于他的创作生涯中。
1766年6月16日,在这位艺术家病逝后,乾隆皇帝特发布一道谕旨,以示对亡者的深切敬仰和悼念,强调了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坚定不移的忠诚、堪称楷模的品格和操守。此外,谕旨也突出了清廷对西方艺术技法的接受和赞赏:“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戴。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旬,著照戴进贤[Ignatius Kögler]之例,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给内务府银叁佰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钦此”[11]。
即使在郎世宁去世数百年后的今天,其艺术遗产仍延绵不断。他的画作流芳于世,为历史学家所研究,为艺术家所赞赏,并继续向我们展示当不同文化在相互尊重和创造性的协同作用下相遇时所产生的深邃之美。他的生平和作品见证了艺术跨越时空的沟通力量,以资后人感知万物中天主的临在,拥抱文化交流的无限可能。
- 参见:李启乐,《通景画与郎世宁遗产研究》,载于 www.dpm.org.cn/Uploads/File/2018/06/15/u5b237189e7e11.pdf。 ↑
- 《礼运大同篇》,见www.confucianacademy.com/load.php?link_id=27616 ↑
- 这件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见 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0989 ↑
-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载于www.gushiwen.cn/shiwenv_9dcf133d25cc.aspx ↑
- 此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见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0375.html。 ↑
- 此作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见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4550.html。 ↑
- 该作品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参见https://fhac.com.cn/consult.html ↑
- https://m.shidianguji.com/mid-page/7426481359461466149 ↑
- 该画作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见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Collection/Detail/3581?dep=P ↑
- 本文作者在此注中提供了款题的中文原文,无需赘述——译者注。 ↑
- 该文本的英译本收录于E. J. Malatesta – Gao Zhiyu (edd.), Departed, yet present. Zhalan the oldest Christian cemetery in Beijing, San Francisco – Macau,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5, 217。中文原文镌刻在位于北京行政学院院内的郎世宁墓碑上。参见 https://www.bac.gov.cn/content/index.aspx?nodeid=303&page=%20ContentPage&contentid=88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