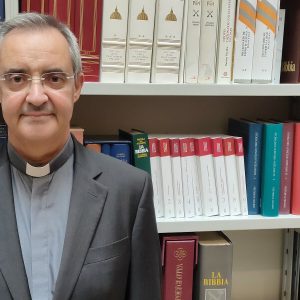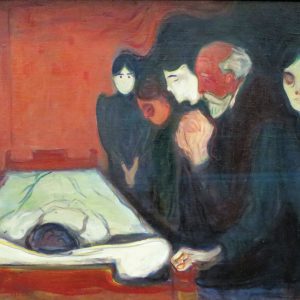大多数开始学习大众传播的学生都熟悉电影《一夜风流》(弗兰克·卡普拉,1934年),由克拉克·盖博和克劳黛特·考尔白主演。在剧情的某个时刻,盖博饰演的角色在换衣服时脱下衬衫,露出没有穿背心的胸膛。学生们听说男性背心的销量因此而急剧下降,这表明电影明星对文化的影响。尽管这个故事很有趣,但这种说法可能缺乏依据,因为这种流行观点并未在销售数据中得到佐证。然而,它确实说明了名人或知名人士似乎对普通人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基于轶事佐证,我们倾向于相信这一点。
首次系统研究媒体影响力的科学研究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保罗·费利克斯·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对广告和政治信念进行了研究。基于一项调查,这位学者及其研究团队确认,信息并不是从大众媒体直接流向最终受众者的;相反,媒体的影响是通过他们所称的“双向信息流”的方式传递的,即那些对大众媒体报道更敏感的人会影响其朋友对购买或投票行为的信念。他们将这一过程称为“个人影响”,因为人际关系至关重要;我们今天所说的“网红”当时被称为“舆论领袖”。
今天围绕社交媒体网红相关的问题直接源于这一传统观念和对影响力的研究。社交媒体网红是“一种新型‘连接者’,通过博客、推特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在他人与公众之间架起桥梁并塑造公众的态度”[1]。这些活跃于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体,似乎能够影响其粉丝的消费选择、投票行为、健康习惯或其他类型的行为。其中部分人因提供此类服务而获得报酬,另一些则成为某产品或企业的非官方代言人。
解释网红
传播学研究人员从多个角度对这一现象做了研究。首先,他们通过分析网站和视频内容,关注网红所表达的言论。其次,他们对在线粉丝进行访谈,了解他们的反应;特别是询问他们为何关注特定的网红,以及是否会根据网红的建议做出决定,例如购物或投票等。有些人关注网红存粹只是为了娱乐,并不一定按照他们的建议行事。第三,从一个备受关注的视角出发,研究人员试图解释网红为何具有影响力。哪些特定特征解释了他们的影响力?其中一些研究遵循了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当年指出的方向,将舆论领袖视为双向信息流的源头,即追随者信任领袖以获取信息并指导其决策。但是,是什么让某人成为舆论领袖的呢?这个术语仅仅描述了一种角色,指出舆论领袖拥有人脉、开展活动、获得回报并引发模仿[2]。这种领导力可以通过面对面接触或“口口相传”来实现。今天的舆论领袖通过各种媒体运作,但这种现象在过去也以某种形式存在,当时涌现了各种品牌代言人,尤其是作为广告代言人的名人与电影明星。
这种通过媒体呈现建立的联系属于研究人员所称的“准社会关系”。准社会关系是指一个人想象与自己不认识的人建立关系,通常是名人,甚至是电影或电视节目中的角色:他会表现得好像那个人是自己的朋友。研究表明,网红越能培养准社会关系,就越有可能影响粉丝的行为。数据表明,感知到的相似性、互动频率、真实性、分享家庭故事以及感知到的可信度等因素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何会发展准社会关系。然而,准社会关系自身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个网红的成功。
在对2007年至2020年间发表的68篇科学论文进行研究后发现,该领域存在至少八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可信度、可靠性、吸引力、专业性、受欢迎程度、准社会关系、友谊感以及与网红的人际契合度。更具体地说,关于成功性影响力的理论解释列举了来源特征(可信度、外在魅力、熟悉度、专业性、可靠性、受欢迎程度、声望)和心理因素(与网红的个人一致性、共情、好感、友谊感、相似性、渴望认同、品牌适应性)以及内容属性(产品差异性、视觉一致性、视觉吸引力、信息含量、互动内容、原创性等)[3]。此外,准社会关系并非发生在一个独立的世界中,而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
另外三种普遍接受的理论模型,被传播研究者用于解释网红产生的影响,主要聚焦于粉丝和媒体。著名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描述了人们为何会转向传播媒体。换言之,该理论研究了人们通过使用媒体满足了哪些需求。例如,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观看电视:获取新闻或信息、娱乐、消磨时间、在家中听到人声等等。该理论认为,人们关注网红是因为他们从中有所收获。除了获取产品或活动信息外,粉丝还满足了对现实感、新鲜感、新奇感、存在感、自主性增强、社区归属感以及“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4]等需求。
议程设置理论(agenda setting)在新媒体研究中被广泛应用,该理论表明,新闻报道的主题即使不能影响人们的实际信念,但会影响人们的谈话内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网红身上:他们讨论的问题和产品会使这些话题对更多的人变得更为重要。这一理论丝毫不能解释网红说服力的成功,它仅仅说明网红放大某些事物重要性的能力,以及在这些事物周围营造一种重要感的能力。与此相关的理论,即“启动效应”(priming),描述了通过媒体呈现的内容和信息如何为受众提供一个背景,从而引导他们根据网红的信息来解读或评估。例如,如果一个网红说某品牌鞋子比另一品牌更舒适,这会让受众者倾向于根据舒适度来评判鞋子。
某些特定品质是否会使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成功的网红?研究人员首先关注的是什么使“舆论领袖”成为领袖,他们识别出若干关键特征,包括知名度、特定价值观的体现、专业能力、社会地位、可信度、吸引力、专业知识、信息内容、影响力(即吸引公众参与的能力)以及社会感染力(即朋友的看法)[5]。一个人具备这些特质越多,其他人就越有可能跟随他。
其他研究人员探求了预示受欢迎程度的心理特征。其中包括不同程度的外向性、可靠性、能力、相似性、吸引力、神经质倾向、亲和力、尽责性、对经验开放、智力投入、受欢迎程度、声望、自我效能以及非语言性互动(如眼神或微笑)[6]。
最后,对影响力的期望本身可能预示着更大的影响。三种要素的结合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循环:假设的曝光(人们假设他人注意到了网红); 假设的影响力(人们假设某个人可以影响他人);以及假设影响力的影响(人们假设影响力是有效的,就像电影《一夜风流》的影评人所假设的那样,尽管有证据表明,对服装的选择不会影响他人)[7]。
一些人将网红的所谓成功归因于他们所使用的媒体的特性。影响力的等式中包含“社交渠道”,即社会中的一系列常识。人们假设与这些知识相一致的信念被广泛共享,并且一定有其来源;网红分享这些信念的程度越高,其影响力就被认为越大。不同的社交媒体渠道,通过促进准社会互动、增强归属感并鼓励自我表达,为用户提供了情感依附的期望,进而使其更倾向于相信网络人物。
各种理论分析均指出,网络人物在影响他人方面存在一种合乎逻辑的途径;同时,这些分析也承认,由于造成这种现象涉及众多变量,直接预测影响力的难度较大,其中包括“媒体的象征意义、信息的模糊性、信息传递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距离、感知到的媒体丰富性、信息接收者的数量和对信息接收者的态度的感知”[8],以及外部因素,如广告和促销(影响销售),还有政治运动(影响政治)。
最后,一些理论家支持一种更广泛的多重影响理论,并认为“第三人效应” ——一种经过广泛验证的理论,提议个体认为媒体内容对他人(“第三者”)的影响大于对自身的影响,从而导致他们高估媒体内容的影响力——放大了人们相信网红的影响力的意愿。
网红研究探讨了什么
几乎在所有社交媒体覆盖的地方都有网红的身影。他们推荐时尚理念、美容产品、宠物护理、家庭活动、书籍和电影、政治观点、健康习惯、祈祷方式、音乐:几乎任何可以发表意见的事物。最近,学者们开始关注市场营销、政治、健康、新闻和生活方式等领域的网红。
社交媒体上最受关注与研究的网红活动莫过于市场营销与销售。企业会聘请网红来推荐他们的产品,当然也想知道哪些人能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通常,企业会出于多种原因使用网红或舆论领袖:为了“提升企业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改善企业声誉、增加虚拟社区中的讨论、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信息以及推广新产品”[9]。企业将对网红的使用融入其市场营销和广告策略中,且在此过程中绝不马虎,因为网红会创建内容、分发内容、担任代言人并推荐产品及其使用方式。
在选择网红时,需要考虑多个因素:与品牌契合度、粉丝数量、人们遵循推荐的可能性等等。另一方面,企业试图限制负面评论的影响。与其他网络在线表达领域不同,营销影响力必须遵守政府在有偿赞助、真实广告以及披露与企业集团关系等方面的规定。监管水平因法律管辖权而异,美国和加拿大要求更为严格,而欧洲和亚洲则较为多变。网红的规范和实践也反映了人们对他们及其活动的期望在文化上的差异,这一点在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中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地的研究中均有记录。
作为产品的网红,粉丝和客户似乎更喜欢普通人而非体育明星或媒体名人,因为他们觉得前者更像自己——也就是说,他们能与之产生共鸣——且不太可能被视为企业代言人。同样,研究人员观察到粉丝数量与参与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换句话说,一开始,与网红的互动会随着其知名度或粉丝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到一定程度后,粉丝数量的增加反而会导致互动减少,这可能再次是因为非常著名的人似乎与普通人差异太大。其他人则指出,粉丝更看重表达的原创性和产品的相关性。
政治网红也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这种兴趣延续了七十年前开始的研究进程,当时研究者首次探讨了影响力以及舆论领袖如何塑造人们的政治观点。尽管仅有少数实证研究测量了这一群体的实际影响力,但这些研究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探索了在新的数字平台上,当人们以创新的方式与他人互动时可能发生的情况[10]。影响力更多地以媒介形式而非面对面互动的形式产生。这带来了对舆论领导力的新理解:除了原有模型中的两个角色——领导者和寻求建议者——数字世界还显示,某些个体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既提供信息又寻求信息。这些双重角色的个体倾向于了解更多新闻、使用更多信息媒体,且比其他人更具政治活跃性[11]。他们常常有意识地试图影响他人并广泛传播自己的观点。
数字政治网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支持特定候选人或政治议题的群体,另一类则是对可能涉及政治议题的生活方式问题发表评论的群体,例如教育、犯罪、健康或住房等领域。后一种影响可以在任何平台上由任何类型的网红产生:例如,当一位专注于育儿的网红评论国家或社区学校的教育政策时,这种影响就会发生。对于这一群体,其中常包括娱乐明星和运动员,他们的政治评论往往是昙花一现,且常被嵌入其他内容中。另一方面,第一类群体——那些专门评论候选人或政治议题的群体——可能由选举活动家或被政治操作者招募的人员组成,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帖子与竞选活动相协调。在这两种情况下,影响力的最佳预测指标是粉丝与网红之间的感知相似性[12]。
研究人员发现,相比市场营销领域,虚假信息或错误信息在政治传播领域的网红中更为普遍,这很可能是因为企业赞助商仅要求提供准确的产品信息,且许多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规定要求“广告真实”。此外,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使许多国家无法对政治言论设置限制。政治虚假信息——研究人员曾将其归类为“宣传”——在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上普遍存在,并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等议题上。西方多个国家的政府情报机构指出,某些形式的政治虚假信息源自与本国利益相左的政府。研究人员还测量了政治网红言论中的不文明程度,并将其与社会身份及个人政治活动范围相关联。
网红研究的第三个领域聚焦于健康传播。与许多关于市场营销和政治领域的网红研究不同,这些研究通常采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试图明确并量化网红传递的信息,特别是涉及公共卫生问题的内容,如新冠疫苗接种或预防疾病的措施。疫情为公共卫生当局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使其能够通过招募网红测试不同信息内容。他们将“专家型网红”(例如医生)与“情感型网红”进行对比。其他研究小组识别出具有影响力的网络的三大功能:提供信息;验证信息;为情绪管理提供情感支持[13]。在美国,一个公共卫生委员会尝试招募网红传播戒烟信息,发现通过更多小网红(粉丝数少于10万)传播信息比通过少数几个非常受欢迎的网红传播信息更有效,并注意到人们更容易信任本地名人。其他研究发现,电子烟上的健康警告会削弱名人鼓励使用电子烟的信息的说服力。
一些教会将使用灵修网红视为其传教使命的一部分
另一个关于网红健康传播的研究领域关注健身和健康实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网红,如那些从事市场营销的网红,可能受到运动器材公司的赞助或与健身房合作。健身领域的网红在激励他人遵循良好的健康习惯方面往往相当成功。最后,如在疫情研究中指出的,网红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提供健康信息,特别是针对传统上得不到完备服务的群体。
许多关于影响力的原始理论最初是基于对舆论领袖如何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政治)新闻的调查而发展起来的,这些公众并未直接受到媒体的影响。近期多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人们确实会效仿那些被认为对新闻更了解的人。这些研究还表明,当今的舆论领袖往往拥有更多新闻来源,并整合这些信息供其追随者参考。
宗教领域同样存在网红。部分教会将影响力实践纳入公共关系或宣传策略,因为他们视“灵修网红”的运用为传教使命的一部分。例如,某教会的传播部门可能会重新编写一位知名宗教领袖的讲道和祈祷文,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旨在引导信徒和寻求真理的人归向天主。其他宗教网红则独立于任何教派或教会运作,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对神之召唤的回应;他们发布关于灵修启迪、教义、福传和娱乐的内容,后者旨在增强与信徒的准社会关系。许多人试图建立一个以爱好为基础的宗教团体,其特点是对信仰的关注更具个人化而非教派化[14]。
公众对网红的普遍印象往往将其与文化网红划等号,即那些从事时尚或媒体行业的人。一些传播学学者对这类人群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在舆论领导力和影响力方面。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粉丝将他们视为朋友或友善的人,认为他们能带来娱乐——使他们变得受欢迎。他们可以通过时尚创新等手段影响他人,但研究人员难以具体识别其粉丝的购买决策。品牌身份、价格以及其他媒体的消费习惯在购买决策中均扮演重要角色。
其他研究也探讨了网红在决定是否观看电影放映中的作用,结果同样不一。人们报告了社交媒体使用、观点、观看电影以及社会资本以“害怕错过”[15]表达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在几乎所有研究案例中,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在解释人们的行为时都扮演了多种角色之一。
对网红的担忧
不断壮大的网红世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涉及影响力的伦理问题,尤其是赞助或付费影响力。影响力模式的原始版本——在“双向信息流理论”中提出——假设影响力是通过面对面互动产生的,通常由朋友或熟人在家庭或社交场合中施加。尽管广告业一直基于此模式,通过让名人代言产品来实现品牌传播,但当今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主要通过陌生人传递,他们的名气往往仅存在网络上;通常,社交媒体粉丝与网红之间仅存在一种准社交关系。无论是社交距离还是过程中的匿名性,都引发了对信任基础以及识别欺骗能力的质疑。
2024年欧盟立法修订显示,仅法国和西班牙制定了要求网红透明及明确区分事实与观点的指导原则,通常适用于产品广告场景。捷克共和国正在制定一份《网红行为准则》,该准则受到了消费者协会的赞扬。尽管美国有涉及广告的消费者保护法,但这些法律在网红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这促使学者呼吁美国也制定一份行为准则。
研究新闻报道中的虚假信息(以美国校园枪击案为例),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当地居民显得更具可信度,而粉丝们能迅速识别出知名但遥远舆论领袖传播的虚假叙述。此类研究结果促使人们呼吁为社交媒体用户制定媒体素养教育计划,以便他们更容易识别虚假信息和付费影响力。这尤其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以及儿童和青少年网红,因为他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网红世界背后运作的机制。
另有学者对“虚拟网红”的使用提出了质疑,即通过动画角色,或者,甚至由人工智能创建的角色来代表公司、品牌或政党。尽管此类网红可能为其赞助方提供更大的控制权,但它们本质上是虚假的且不透明的,导致难以追溯其任何道德或法律责任。
结论
19世纪费城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老板约翰·沃纳梅克曾说过:“我知道我一半的广告有效,但不知道是哪一半。”这句话似乎对研究网红具有现实意义。尽管关于网红影响力的轶事证据层出不穷,但支持其有效性的实际证据却少之又少。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观众一样,人们总愿意相信名人——甚至是微名人——能够说服他人。但更深入的分析似乎表明,网红只是解释人们行为的众多因素之一。大部分针对粉丝收集的数据所评估的是购买、投票或认同的意图,但并未考察人们是否真正付诸行动。传播研究在揭示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网红、什么吸引粉丝以及影响过程本身取得了许多进展,但难以衡量实际影响力。
该调查凸显了传播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关于网红的研究都考虑了文化因素:影响过程在越南、伊朗、法国、西班牙、捷克共和国、韩国、美国等国家存在差异。至少在这一研究领域,研究人员避免提出单一的通用理论。
对网红研究的分析,即使在较短时间内,也清楚地表明了跟上快速发展的社交媒体技术所面临的困难。仅在过去10年间,网红就出现在了YouTube、Facebook、X、Telegram、Instagram和TikTok等平台上,有时甚至超越了这些平台。社交媒体用户偏好的变化以及用户年龄的快速更迭,使得企业和研究人员都难以跟上步伐。社交媒体的结构也改变了原有的影响力结构,这些结构原本假设影响力是通过面对面的个人互动产生的。在线评论、分享和关注的便捷性意味着影响力通过多种媒介以非传统方式展现,这往往超出了传统影响力理论的预测范围。
最后,不同社交媒体渠道及其使用方式的多样化,引发了关于“网红”这一术语是否在所有平台上指代同一现象的讨论。尽管研究人员已将诸多传统理论和模型应用于其研究,尽管可以辨别出一种普遍的相似性,但仍可注意到,在网红所处的不同领域(市场营销、政治、公共卫生、娱乐、宗教等),每个领域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使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成为成功网红的因素,无法轻易转移到其他领域。正如学者们常说的,“尚待进一步研究”。
- K. Freberg – K. Graham – K. McGaughey – L. A. Freberg, «Who are the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A study of public perceptions of personality», i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7 (2011/1) 90. ↑
- 参见 K. Jungnickel, «New methods of measuring opinion leadership: A systematic,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2018) 2702. ↑
- 参见 D. Vrontis – A. Makrides – M. Christofi – A. Thrassou,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marketing: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grative framework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45 (2021/2) 628 s. ↑
- 参见 C. Lou – C. R. Taylor – X. Zhou, «Influencer marketing on social media: How different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fford influencer-follower relation and drive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in Journal of Current Issues & Research in Advertising (Routledge) 44 (2023/1) 60. ↑
- 参见 G. Weimann, «The influentials: Back to the concept of opinion leaders?», 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5 (1991/2) 267-279; S. Aral, «Identifying social influence: A comment on opinio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ontagion in new product diffusion», in Marketing Science 30 (2011/2) 217-223; T. Gnambs – B. Batinic, «A personality-competence model of opinion leadership», in Psychology & Marketing 29 (2012) 606-621; D. Bakker, «Conceptualizing influencer marketing», in Journal of Emerging Trends i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1 (2018/1) 79-87; C. Ki – Y. Kim, «The mechanism by which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persuade consumers: The role of consumers’ desire to mimic», in Psychology & Marketing 36 (2019) 905-922; N. Jung – S. Im,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media marketing: Influencer characteristics, consumer empathy, immersion, and sponsorship disclosur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40 (2021) 1265-1293. ↑
- 参见 T. Gnambs – B. Batinic, »A personality-competence model of opinion leadership,« cit., 611. ↑
- 参见 H. Cho – L. Shen – L. Peng, «Examining and extending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hypothesis in social media», in Media Psychology 24 (2021/3) 413-435. ↑
- L. K. Treviño – J. Webster – E. W. Stein, «Making connections: Complementary influences on communication media choices, attitudes, and use», in Organization Science 11 (2000/2) 163-182. ↑
- B. Bahar, «La collaboration des entreprises avec des leaders d’opinion: une étude qualitative. Companies Collaboration with Opinion Leaders: A Qualitative Study», in Ileti-s-Im 30 (2019) 1. ↑
- 参见 M. J. Riedl – J. Lukito – S. C. Woolley, «Political influencers on social media: An introduction», in Social Media + Society 9 (2023/2) 1-9. ↑
- 参见 J.-Y. Jung – Y.-C. Kim, «Are you an opinion giver, seeker, or both? Re-examining political opinion leadership in the new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2016) 4439-4459. ↑
- 参见 B. Naderer, «Influencers as political agents? The potential of an unlikely source to motivate political action», in Communication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8 (2023/1) 93-111. ↑
- 参见 A. Wagner – D. Reifegerst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imes of Covid-19: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media coverage in a pandemic crisi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38 (2023) 1014-1021. ↑
- 参见 B. G. Smith – D. Hallows – M. Vail – A. Burnett – C. Porter, «Social media conversion: Lessons from faith-based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for public relations», in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33 (2021/4) 231-249. ↑
- A. C. Tefertiller – L. C. Maxwell – D. L. Morris II, «Social media goes to the movies: Fear of missing out,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motivations of cinema attendance», in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 (2020/3) 378-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