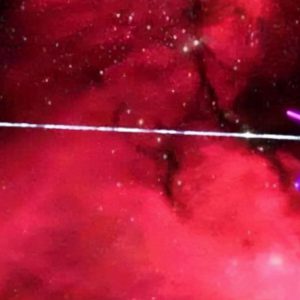生平
1914年8月26日,胡里奥·弗洛伦西奥·科塔萨尔(Julio Florencio Cortázar)出生于布鲁塞尔南部的一个小村庄伊克塞勒(Ixelles)。今年是其诞辰110周年和去世40周年纪念。科塔萨尔是一名外交官之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家人逃往瑞士,在那里度过了战时的大部分时光。随后,他又逃往巴塞罗那避难,在四岁时,移居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到达阿根廷几年后,其父亲抛弃了家庭,他跟着母亲、姨妈和姐姐长大。他从小体弱多病,对文学饶有兴致,在9岁时便已读过儒勒·凡尔纳(Giulio Verne)、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和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他在18岁时完成了高校学业,于1935年获得了文学学位。虽然希望继续攻读哲学,但他为了避免为家庭带来经济负担而决定就业。那一时期,他曾在阿根廷不同城市尝试教师职业。
从1946年起,他因抗议胡安·贝隆(Juan D. Perón)当选总统而放弃了教学,开始为阿根廷图书商会工作。在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以下作品:第一部短篇小说《被占的宅子》(Casa tomada),发表于由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负责出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年鉴》(Los Anales de Buenos Aires)杂志上;关于英国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评论文章;短篇小说集《彼岸》(Otra orilla),该书后来才被出版。1948年,科塔萨尔正式成为英语和法语译者。那是科塔萨尔与各种文学杂志密切合作的年代,他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Bestiario)也在此期间问世。1951年,这位作家决定移居巴黎,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与此同时,他也曾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游历。
。他曾于1961年访问古巴并担任文学奖竞赛评委。从那时开始,他心中萌生了对拉丁美洲政治的浓厚兴趣。。他在这方面的努力通常体现为将其作品版税捐作政治犯援助基金,这一努力于1974年步入巅峰:那一年,科塔萨尔与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和阿曼多·乌里韦(Armando Uribe)等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被任命为罗素二世法庭[1]成员。该法庭由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作家让·保罗·萨特等人创立,于1966年至1967年期间首次开庭,并于1974年至1976年期间第二次–也就是科塔萨尔参与的那一次–在罗马和布鲁塞尔举行庭审,查究拉丁美洲的政治局势,尤其是关于侵犯人权方面的问题。在此后数年中,这个独立的舆论法庭继续开展工作,研究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其他敏感地区和问题:如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刚果、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问题。
科塔萨尔的政治承诺是使作家重获自由,他曾身居前列,争取使希伯托·帕迪利亚(Heberto Padilla)和胡安·卡洛斯·奥内蒂(Juan Carlos Onetti)获释。科塔萨尔与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之间的冲突在1976年至1983年期间变得极为激烈,以至他的某些短篇小说被禁止在国内发行,因为这些小说的立场是对悲惨的失踪者(desaparecidos)现象表示斥责:在那些年中,这一现象造成的受害者高达15,0 00人。
从1981年开始,这位作家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同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授予他法国公民身份;1983年,科塔萨尔得以在独裁政权垮台后最后一次故国重游,受到许多仰慕者的热烈欢迎;1984年2月12日,他在原配奥罗拉·贝纳德斯(Aurora Bernárdez)的陪伴下在巴黎去世。
科塔萨尔文学创作的三个阶段
这位阿根廷作家在伯克利(Berkeley)大学于1980年举办的八场文学讲座中将自己广泛而多样的创作演变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这些讲座后来以《文学课》为书名结集出版。这三个阶段的排列以时间为序,体现了作家的主要关注点、态度和兴趣。在此,我们以其本人所选择的命名来介绍这三个阶段:美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历史阶段。
美学阶段可以追溯到其青年初期,也就是当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在这一阶段,他对文学的热爱与对阅读的偏爱密不可分,其中美学和文学性是两个尤为重要的方面。作家表示说:“我记得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这些阿根廷年轻人(porteños是我们对其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称呼)都是美学化程度很高的人,他们专注于文学的审美、诗意价值以及各种精神上的共鸣[…]。当时,我和同龄的年轻人既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处于边缘,也没有认识到正在自己身边发生的那段充满悲剧性的历史,因为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感知发自一个疏离的视角,有着精神上的隔阂”[2]。
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反映了作家对生活基本问题的更多关注,其中尤其是一种对生存的关注,这是一个向世界和他人开放但仍带有私密与个人倾向的阶段。“我沿着这条道路进入了自己有点迂腐地称其为形而上学的阶段,这是一个缓慢、艰难而且非常初级的自我探索,因为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倾向于哲学,这种探索所针对的是人:并不是说人作为一种单纯的生存和行动的存在,而是作为哲学意义上的存在,作为命运,作为一段神秘行程中的道路”[3]。向第二阶段过渡的作品是1959年的短篇小说《追寻者》,科塔萨尔所著短篇中篇幅最长的一部。然而,最能体现“形而上学”创作方法的作品是196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跳房子》(Rayuela),这部作品是科塔萨尔长期酝酿的结果,被许多人视为其代表作。关于主人公霍拉西奥·奥利维拉(Horacio Oliveira),他指出:“这是一个专注于本体论问题的人,这些问题触及人类存在的根本,即:为什么这一从理论上而言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能力和一切积极因素创造积极社会的人类,最终却功亏一篑半途而费,或者时进时退。
第三阶段是历史阶段,在此期间,作家果断地向他人和社会敞开心扉,对世界做出承诺。这是更为公开的阶段,去聆听世界上的问题、疑问和伤痛。科塔萨尔指出:“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即历史阶段,其前提是打破那种充斥于奥利维拉的探索中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因为尽管他确实在思考自身的命运作为人的命运是什么,但一切都以其个人及其喜怒哀乐为中心。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不要只把近人当作自己认识的一个或多个个体,而是要将他视为不同社会整体、各民族、文明、人类的总合”[4]。
据作家本人所言,上述三个阶段并不会在依次推进中被抹消,而是总会在下一个阶段的延续中有所保留[5]。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在科塔萨尔之后,切身关注重大政治和历史问题这一愿望本身–在那些年里,这些问题是引起国际舆论和许多知识分子热烈讨论和关注的中心–要求我们对文学和美学的基准保持更大的警惕性,以免那些有担当感的文学沦入贫乏和平庸[6]。此外,仍需指出的是,科塔萨尔对三个阶段的考虑并不显示一种价值判断,就好像“形而上学阶段”肯定要比文学阶段略胜一筹,而历史阶段总是比前两个阶段更受欢迎。科塔萨尔表示,重要的是,首先要保障作家享有探索和自我表达的自由;其次,作家应各尽所能,因为只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才能促进人类的成长和自由[7]。
作品及其与音乐的关系
科塔萨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他的爱好和作品不胜枚数,反映了其丰硕成果。他是公认的重要的法文和英文翻译[8]、诗人和散文家,著有短篇小说[9]、长篇小说[10],并恢复了年鉴的传统,即编纂杂文合集[11]。此外,他还酷爱探戈[12]、爵士乐和拳击,而这些喜好也构成了他的某些最佳短篇小说的背景、主题和构思元素。
首先,不能不提的是长篇小说《迫害者》(Il persecutore),主人公约翰尼·卡特(Johnny Carter)是音乐家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化名。“在胡里奥·科塔萨尔的作品中,音乐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既是一种隐喻,也是一种完全的创作参照模式。在《缅因人》(Le menadi)、《乐队》(La banda)以至《会合》(Riunione)等短篇小说中,正是音乐世界的介入打破了现实的常规视角,使它们显得相对”[13]。尤其是爵士乐[14],在某些评论家看来,爵士乐构成了科塔萨尔散文的音乐“模式”,科塔萨尔本人曾明确地将其作为其散文的鲜明特征之一[15]:“最好的文学作品总是take[16],是一种隐含在执行中的风险,一种危险的边缘,它为驾驶和爱增添情趣,尽管也带来较大的损失。[…]我不想写别的,只想写takes”[17]。
对于这位阿根廷作家而言,语句以某种形式“鸣响”,而发声的共鸣是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对语法、语言和标点的选择标准[18]。遗憾的是,翻译版本并无法向我们传达这一恰是作家创作之核心的特色[19]。正如他本人所言:“我常常发现一部译文无懈可击,其中虽然对原意的传达非常到位,没有任何遗漏,但并不是我以西班牙语经历并写下的故事,因为它缺少脉动,而读者对节拍是敏感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对什么敏感的话,那就是对深刻的直觉,对非理性的事物”[20]。
拳击也是科塔萨尔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如同海明威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等其他作家。拳击手被视为角斗士,是全力以赴且毫不退缩者的形象。科塔萨尔致力于拳击世界的短篇小说包括《小公牛》、《曼特基拉之夜》以及《第二次旅行》。
短篇小说与虚幻元素
如果说科塔萨尔享誉国际的作品无疑是1963年的长篇小说《跳房子游戏》,那么他的短篇小说则尤其能够使我们领略到这位作家风格的演变、兴趣的广泛性、语言的可塑性以及散文的实验性特征,这种实验性甚至是俏皮的。最后一个特征体现于两部以讽刺笔调为特点的作品中,它们是1962年的《克罗诺斯和法玛斯的故事》(Historias de cronopios y de Famas)和1979年的《这样的一个卢卡斯》(Un tal Lucas)中[21]。《克罗诺斯和法玛斯的故事》在国际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22],但也构成了这位阿根廷作家文学创作中一个分隔号。我们在这本书中读到是在短短几周中写就的故事,其中大部分创作于1953年科塔萨尔在意大利逗留期间。当几个月之后感到这些故事变成了一种“自动”写作的结果时,他中止了这些故事的写作。可以说,“短篇小说”这一体裁是其文学创作的主线,也是检验其变更的试金石。
科塔萨尔是拉美作家队伍中的领军人物,这些作家于20世纪60年代发起了“拉美文学爆炸现象”,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胡安·卡洛斯·奥内蒂(Juan Carlos Onetti)和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科塔萨尔与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通常号称具有“拉美现实主义”的魔幻特质,,而科塔萨尔则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一称号进行了具体化和“个性化”。事实上,与其说是魔幻现实主义,不如称其为“象征现实主义”,即作为更深层次现实之象征的现实,而这一更深层次现实的展现不仅更深刻,也更真实。这位作家指出:“让我来解释一下:我所说的象征现实主义,是指当一部短篇或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主题和发展都是读者可以接受的、完全真实的,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他们会意识到,在严格的现实主义表象之下,还隐藏着另一些内涵,它们也是现实,甚至是更加真实、更加深刻、更加难以把握的现实。[…]于我而言,在本世纪中,我所说的象征现实主义的无可争议的大师是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23]。这位阿根廷作家将小说《审判》视为“象征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典范,该小说的故事情节远非“牵强附会”(一个无辜者被指控犯下了一桩不为他所知的罪行)。科塔萨尔回顾了某些人在暴力(和酷刑)的心理和生理压力下被迫交代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行的案例,而这些案例与幻象根本不着边际。
科塔萨尔风格的一个主要方面来自他对虚幻元素的概念,于他而言,虚幻元素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现实的“模式”。这位作家宣称,“如是,我意识到在发生些什么:对我来说,从童年开始,虚幻就不是众人心目中的虚幻;在我看来,它是一种现实的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一本书或一件事情体现出来,无论对我还是对其他人都是如此,但它并不会打破既定现实”[24]。如果虚幻是现实的一种模式,那么拥抱它、接纳它、考虑它就成了相信它的理智和情感方面的姿态。只有那些接受这一层面的人才能说他们是张开眼睛观察世界的:“我相信,那时的我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比现实主义者更现实,因为像我朋友那样的现实主义者只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现实,而其余的一切无非虚幻。我所接受的是一个更大、更有弹性、更扩散的现实,一切都尽在其中”[25]。
对于基督徒读者,这些话不会使其无动于衷。作为一种“开放”的信仰,难道这不意味着增强观察现实的能力,以感悟“居住于”、“融汇于”、“高于”现实的意义和存在吗?某些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希望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信仰的镣铐中“解放”出来,但实际上却反将人们的心灵禁锢在一种狭隘的视野中,对于这些立场,即使科塔萨尔并未宣称自己是一名基督徒作家,但阅读他的短篇小说仍可成为对“可能”的抵抗剂的对抗,而这种“可能”的命名正属于信德的目光。正如这位阿根廷作家的短篇小说展示了现实“被掩盖的”褶皱,信德也明示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盼望和爱,并满怀信心地生活。正是在对这一维度的接受与探索的过程中,科塔萨尔提出了关于时间的问题[26]:时间是什么,如何运作;同时,他也提出了关于“可见之外”存在着什么的问题,例如,音乐及其对情绪所产生的触动与共鸣作用揭示了这种“可见之外”的存在。难道信仰对神秘的向往不能通过类似的方式得以表达吗?
除此之外,其他反复出现的主题包括梦(《远方》、《河流》、《仰卧的夜晚》、《以水为背景的故事》、《讲给我自己的故事》、《不遇》、《以鲍比的名义》),伪装(《母亲的来信》、《病人的健康状况》、《笔记本中的文字》、《停留结束》),灵魂交换(《远方》、《蝾螈》、《秘密武器》),儿童与少年心目中的生活和爱情(《动物寓言集》、《毒药》、《午餐后》、《游戏结束》、《科拉小姐》、《西尔维娅》、《午睡》、《她在我身边躺下》、《以鲍比的名义》),爱情及其陷阱与成人幻觉(《喀耳刻》、《天堂之门》、《夏季》、《变幻的灯光》、《信风》、《硬币的两面》、《讲给我自己的故事》、《不遇》)以及公民和政治承诺主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谈到这些主题。
我们在此提供的划分仅涉及一定数量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应被视为纯粹的范例。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会发现这里所引用的某些短篇小说在元素和构成上的层次顺序超出本文的意图范畴。
短篇小说的特点:意义、强度与张力
科塔萨尔认为,很难对“短篇小说”进行分类。这一体裁历史久远,在19世纪的欧洲已经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形式。不过,长篇小说作为另一种现代及当代叙事模式而发展和推广起来,夺取了短篇小说的一些光彩。长篇吸引并耗费了大量对其进行探索、分类和研究的文学理论思考的精力。相比之下,短篇小说所享有的空间和关注度可谓少之又少。
科塔萨尔认为,短篇小说的结构与限度的概念有关。这一说法值得强调,因为这位作家本人所选择的术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与其说是形式(forma),不如说他所谈的是结构(struttura),因为结构呼应作者内心深处的意图,而形式也可以在不经过预先构思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生成。这位作家不止一次地将短篇小说比作一个球体,一个成功的短篇小说的形象:“我有时将短篇小说比作球体,一个完美的几何形体,因为它完全封闭在自己内部,其圆周上无限多的点都与看不见的中心点等距。[…]那么现在,既然短篇小说有内在的、构思结构上的义务,即无需保持开放,而是像球体一样在封闭自身的同时保持一种振动,向外投射某种东西,那么,这个将被我们称之为生动再现的元素产生于其他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我看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短篇小说取得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特征”[27]。
因此,短篇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简短的叙事。当篇幅超过一定页数时,文本就会发生变化:在法国被称为“nouvelle”,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被称为“long short story”。根据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著名的“开放式作品”定义,短篇小说是封闭式的,这与(长篇)小说的开放式秩序正好相反。如果说小说家可以通过“积累”和增加情节的方式进行创作,并在“离题”中赋予–或者说可能赋予–故事和人物以深度,那么短篇小说家则必须通过减少和选择细节和特征的方式进行创作。
短篇小说作者的首要选择–这也是短篇小说的一个特征–在于所叙述情节的意义。科塔萨尔将作家称为“痴迷的捕食者”[28]。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或安东·契诃夫(Anton Čechov)等伟大作家将日常生活中的平淡情节转化为对人类境况的深刻体悟,揭示了最普遍的社会或历史状况中的“特殊性”。“当一部短篇小说具有意义时,便会以其迸发出的精神能量突破自身的界限,霍然照亮某些事物,而这些事物远远超出它所叙述的琐碎、甚至微不足道的轶事”[29]。某种事物“喷涌而出”,并形成“日常中的一道裂缝”。
科塔萨尔用两个意象来表达短篇小说的“意义”。第一个意象涉及视觉艺术领域:假设长篇小说好比电影院里的影片,那么短篇小说就好比一张照片。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认为,摄影艺术是一种悖论,它以某种方式在设定种种限制的同时剪裁现实的某一个片段,但这种剪裁旨在“引爆”现实,从而打开一扇通向更广阔现实的大门,“就像一个动态的视觉 ,在精神上超越了镜头的视野范围”[30]。短篇小说–摄影类似–就像发酵的酵母,将智慧和敏感映射于“超越”的事物上,因此必须被吸收,而不是被理解。“有意义”的短篇小说是越出表土层而发芽的种子,“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短篇小说是“苍天大树沉睡中的种子”[31]。科塔萨尔将“有意义”的条件描述为“特殊性”,一种神秘的磁铁般的能力,能够凝聚作家(和读者)以悬浮或液态形式存在的经验、图像、感觉、思想及情感,它们的存在通过短篇小说而被揭示。短篇小说建立与他人的关联,开创一个关系的世界,启动“一种促使我们走出自我的动力,进入一个更美、更复杂的关系系统”[32]。
科塔萨尔用来定义短篇小说体裁的第二个意象是擂台上的搏击。长篇小说好比一个在拉开距离的比赛中“以点数取胜”的拳击手,而短篇小说则是以击倒(knock out)取胜的拳击手。仅仅有意义是不够的,作家还必须巧妙地处理所选择的主题。
短篇小说–及叙事–也是一个技巧(métier)问题,是一个这方面的能力问题,是一个营造强度与张力的问题。作家必须选择最适合主题性质的形式和表现元素:写短篇小说–及叙事–也是一个技巧(métier)问题,是一个这方面的能力问题,是一个营造强度与张力的问题。作家必须选择最适合主题性质的形式和表现元素:写什么和如何写必须和谐一致。这重新涉及到我们已在上文中提到的科塔萨尔所说的“音韵”的价值。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如同“从表达意愿到表达本身之间的语言桥梁”[33]。强度从所有被省略的过渡和补充中产生,是与强烈、明显、确定的行动相一致的秩序。另一方面,其他作者则注重短篇小说的内在张力[34] ,虽然这些小说中并不会发生任何重大事件,但却有一种可以感受到的波浪的积聚和发展,它将在结尾处使读者被打动。
此外,除了科塔萨尔指出的三个特征,我们还希望从他的著作中推断出另一个特点,也就是作家的志向以及短篇小说作为一种回应和责任的“回应责任性”。科塔萨尔断言,没有任何一个有意义的主题是纯粹的(tout court),因此可以通过其本身的意义及对它的处理而赋予短篇小说和文学本身以意义。这位阿根廷作家借用了这样一个意象,即:“某位作家和某个主题在某一特定时刻所结下的神秘而复杂的联盟”[35]在短篇小说和读者之间不断复生。而在此之前,某种吸引住作者的东西将自己交付于他的手中,以求化身为文字:作者因此也要对它负以责任。。在他为这一努力而创作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回顾《索伦蒂纳姆的启示》、《剪报》、《第二次》、《噩梦》、《夜间学校》等,这些作品涉及政府暴力主题,谴责专制军事政权,尤其是“失踪者”这一悲剧事件。当时,阿根廷军政权禁止出版《索伦蒂纳姆的启示》和《第二次》,科塔萨尔因不愿将这两部作品从1977年的作品集《任何一个人》(Alguien que anda por ahí)中删除而被迫在墨西哥出版了这本书。
文学与物理定律的不确定性原理
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卡尔·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于1927年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指出,在量子力学中,不可能同时准确无误地测量定义基本粒子状态的属性。例如,假若我们能绝对精确地确定其位置,那么我们对它的速度就会有最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原理还指出,从概念的角度来看,测量的科学家绝不能被视为纯粹的旁观者,而是会以一种无法计算的方式影响被观测对象,从而产生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对此,科塔萨尔在伯克利大学的八场讲座中的第二场中这样回顾道:“当一个人达到研究的顶峰,达到数学和物理学的可能性之巅峰时,便会打开一个不确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事物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就连精确的数学定律也不能像在较低层次时那样应用了”[36]。此外,他还警告说,类似现象同样会出现在某些文学作品中:在达到奇幻或诗意元素的表达极限之后,“人们进入了一个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不确定的领域,同时,一切事物都具有巨大的力量,即使在不曾被揭示的情况下,也似乎在向我们传达暗示和征兆,让我们继续去探寻并且觉得自己已经走在半路上,这就是奇幻文学在它名副其实时必会提出的”[37]。
文学帮助我们在现实中显得模糊和边缘的地方探索和认识事实。难道信德不也一样吗?当我们以信德的目光观察世界时,会看到穷人、病人、被排斥者,而大多数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因为这会使他们陷入危机。当现实变得难以捉摸时,我们也乐于将信仰想象为一种有助于认识和推动它的力量。难道诸如耶稣关于真福八端的教导(参见玛 5:1-12;路 6:20-23)不包含某种揭示一个更高的层面并使现实改观的“奇幻”元素吗?
- 罗素法庭最初又名“国际战争罪法庭”,有时也被称为“罗素·萨特法庭”,是一个舆论法庭,一个独立的非司法机构。它由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于1966年11月创立,其最初目的是调查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此后,该法庭又继续召开了下述庭审:1974-1976年关于拉丁美洲独裁政权侵犯人权问题(罗马)的罗素第二法庭;1978年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职业禁令问题(法兰克福)的罗素第三法庭;1980年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种族灭绝问题(鹿特丹)的罗素第四法庭;1982年对刚果事件中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政权罪行的审判;2001年关于精神病学中的人权问题(柏林);2003-2005年关于伊拉克军事侵略(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的布鲁塞尔法庭;2009-2014年关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违反国际法问题(巴塞罗那、伦敦、开普敦、纽约、布鲁塞尔)的庭审。 ↑
- 参见J. Cortázar, Lezioni di letteratura, Turin, Einaudi, 1980, 4。 ↑
- 同上,第7页。 ↑
- 同上,第9页。 ↑
- 参见同上,第17页。 ↑
- 参见同上,第18页。 ↑
- “如果说我为自己、为写作、为文学、为所有作家和所有读者捍卫些什么,那就是作家将其良知及个人尊严引导他写的东西投诸于笔下的主权自由”(同上,18)。“如果说作家在意识形态或政治承诺方面能做些什么的话,那就是为读者提供的文学作品不仅要值得一读,而且同时在时机成熟或出于作家的决定的情况下融入一种并非纯属文学性质的信息”(同上,19)。 ↑
- 除了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即使在今天,他的译本仍被认为是这位美国作家作品的最佳卡斯蒂利亚语译本),科塔萨尔还翻译了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鲁滨逊漂流记》)、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亨利·布雷蒙(Henri Brémond)、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小妇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哈德良回忆录》)。 ↑
- 1951年的《角斗士》(Bestiario);1956年的《决胜局》(Final del juego);1959年的《秘密武器》(Las armas secretas);1956年的《万火归一》(Todos los fuegos el fuego);1974年的《八面体》(Octaedro);《有人在周围走动》(Alguien que anda por ahí),1977年;《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Queremos tanto a Glenda),1980年;Deshoras(《失联》),1982年;La otra Orilla(《另一片海滩》),1994年,遗作,由1937年至1945年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组成。 ↑
- 科塔萨尔共出版了以下六部长篇小说,其中有四部是他在世时出版的:《中奖彩票》(Los premios,1960年)、《跳房子》(Rayuela,1963年)、《武装用的62型》(62 Modelo para armar,1968年)和《曼努埃尔之书》(Libro de Manuel,1973年)。其余两部遗作《娱乐》(Divertimento,写于1949年)和《考试》(El examen写于1950年)皆于1986年出版。 ↑
- 这些作品由散文、诗歌、笔记、图画和照片组成,其中有三部作品尤为突出:1967年的《八十个世界一日游》(La vuelta al día en ochenta mundos);1969年的《最后一轮》(Ultimo round);1983年与第二任妻子卡罗尔·邓洛普(Carol Dunlop)合著的《宇宙高速驾驶员》(Los autonautas de la cosmopista)。 ↑
- “后来,我开始发现流行的民间音乐:探戈,在阿根廷,我们那一代人并不喜欢探戈,因为它被认为是庸俗的。我发现了探戈,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外,探戈的文字也使我在对流行语的认识上受益匪浅,了解到人们以诗歌抒发自己的情怀。有时候,卡洛斯·加德尔(Carlos Gardel)的探戈甚至会比阿索林(Azorín)关于语言技巧的文章更胜一筹)”(J. Cortázar, Lezioni di letteratura, cit., 105 s)。 ↑
- E.Franco, Nel giro del giorno in ottanta mondi, in J. Cortázar, I racconti, Torino, Einaudi, 2014, XVIII-XIX. ↑
- 参见J. Cortázar, Lezioni di letteratura, cit., 105 s. ↑
- 参见E. Franco, Nel giro del giorno in ottanta mondi, cit., XVIII s. ↑
- takes是同一首乐曲在用于发行的最终录制版本之前的不同录制。爵士乐的结构以固定主题的即兴演奏为基础。因此,每一次即兴演奏皆因不可复制而是独一无二的。它是预定规范与违规的共同产物:“策划与本能、放弃与控制、灵感与纪律、技巧与狂乱”。参见E. Franco, Nel giro del giorno in ottanta mondi, cit., XX. ↑
- J. Cortázar, I racconti, cit., XIX s. ↑
- 参见同上,Lezioni di letteratura, cit., 100-104. ↑
- 参见同上。 ↑
- 同上,第10页。 ↑
- 参见E. Franco, Nel giro del giorno in ottanta mondi, cit., XXIV-XXVIII。科塔萨尔非常注重对喜剧和幽默的区分。前者旨在娱乐而不矫揉造作或“进一步影射”,后者则亵渎、解放、揭露、摧毁僵化的立场和基座,通过破坏而建设。参见J. Cortázar, Lezioni di letteratura, cit., 107 s。科塔萨尔所指的幽默作家是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ández):参见同上,109 s。 ↑
- 参见同上,126 s; 133 s。 ↑
- 同上,第81页。 ↑
- 同上,第30页。 ↑
- 同上,第31页。 ↑
- 例如,《迫害者》是一部探索这一维度的短篇小说,其中对时间的展现借助于电梯、待装满的袋子以及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的地下车程等画面。在时间维度的处理方式上,我们还可以列举以下短篇小说:《魔鬼的口水》(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受其启发而拍摄了影片《放大》[Blow up]);《黄色的花》;《正午的小岛》;《万火之火》;《另一片天空》;《在那里》,《但在哪里》,《如何》。 ↑
- J. Cortázar, Lezioni di letteratura, cit., 15 s. ↑
- 同上,Del racconto breve e dintorni, in I racconti, Torino, Einaudi, 2014, 1278. ↑
- 同上,Alcuni aspetti del racconto, in I racconti, cit., 1266. ↑
- 同上。 ↑
- 同上,第1268页。 ↑
- 同上。 ↑
- 同上,Del racconto breve e dintorni, cit., 1277. ↑
- 同上,Alcuni aspetti del racconto, cit., 第1270页。 ↑
- 同上,第1268页。 ↑
- 同上,Lezioni di letteratura, cit.,第44页。 ↑
-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