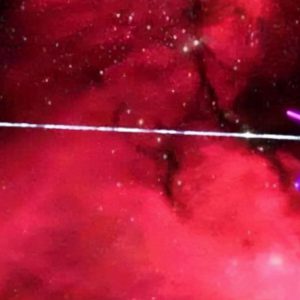教宗方济各的通谕《祂爱了我们》(Dilexit nos,简称DN)表达了对耶稣圣心的敬礼,并将其融入到对“心”这一概念在不同语言及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的导言性精彩默想中。当然,文本中相关的表述主要引自希腊语和圣经。教宗方济各强调:“心”字所指代的是中间部分,生命的最深处,也是思想与情感的交汇处,从而使人—身、心—整合为一(参见DN 3)。于今,谈到“心”时、大胆使用“心”这个概念意味着将我们每个人的注意力引向一个隐藏的深处,引向我们生命最深邃的所在,而不是引向那些所谓的“清晰明确的概念”,例如意志、自由、理性(参见 DN 9-10)。
在此,我们拟通过介绍另一个心性传统的研究而对教宗方济各通谕之构思框架的基本前提做出一个补充,这一传统就是西汉末年之前(大致与基督教纪元伊始的同时期)的汉语文献,其中学者们对“心”这一概念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1]。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心”的主题既已贯穿中国思想的各个领域,包括人类观、天人关系、伦理、政治、医学,等等。此外,不同文献作者对此主题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心”的主题包罗万象,对概念的理解因其所处的不同思想体系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细微差别。
一个兼顾心理与生理的概念特征
“心”字是汉学家们所热衷于探讨的汉字之一。有人认为,不应简单地将其翻译为“心”,因为这会将西方语境中的情感、感觉等因素投射到这一概念,而古代中国将“心”这一器官视为思考的中心,因为它在人体器官中居于“君之位”,正如《管子》(编纂于西汉时期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其内容可追溯至更早时期)的《心术上》所言:“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因此,“心”字更应译作“精神”(spirito-mind)。
“在古代中国,“心”作为器官被视为决策之舍,因为它在人体中占据君主之位。
这一点可以通过佛教文献(其成书时间晚于《管子》)而得到印证,这些典籍为较准确地翻译印度概念而赋予了汉字一种技术性意味。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在古代中国,“心”首先是指心脏这一生理器官,其象形字是对心脏器官的概略描绘,突显了心包膜和主动脉。心与肝、脾、肺和肾并列为人体的五大主要器官。当然,心也是思维活动之所在,但将其译为“精神”既有掩盖其生理基质之不足,也同样会掩盖心脏器官在整个人体中心理和“思维”(mentale)的作用——这是整个中医体系所强调的心的作用。在盎格鲁撒克逊版本中常见的“心-神”(heart-mind)译法则较为恰当。同样,也可以优先选择某些强调“良心”内涵的译法。实际上,在必要的澄清后,即便保留“心”这个简单的概念也无实质障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祂爱了我们》所充分展示的,许多西方文本同样将“心”视为思想与情感的所在,是二者在未产生任何分离前的根源性所在。
然而,对于下面的一段文字,“心-神”这一译法将遗失“心”字令人惊叹的直指含义:“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十一)。
于孟子而言,心是指南针,是辨别是非的关键器官。它是否铭刻在一个具象化的自我,即“作为身体、自我的神”?一些中国思想家还区分出另一种实体,即神/神灵(与前面的身同音但不同形)[2]。在汉语概念“神/神灵”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与依纳爵·罗耀拉在《神操》中所使用的概念酷似的观念:大多数文明(或许所有文明)都力求达到一种难以把握的实相,它同时外在于人又内在于人:一种多元而统一的实相——一个善神与一个恶神,或是多个善神与多个恶神,是某种贯通于我们却又无法被我们掌控的存在[3]。汉字“神”的字形拼写中暗示着一个向上下两个方向持续延伸的动力。在人身上,这些精神属性必须逐步得到净化和提升;我们必须使它们朝着本真发展,正如《淮南子》第七章中所言[4]。
心、气、天
与含义模糊且非为所有思想家所采用的“神灵”概念不同,“心”在所有中国古代文献中被视为人之所特有。此外,凡是开始向内心深处探寻的人,都会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类别,与共享相同力量和同一局限性的生灵共生共存,因为人类拥有与普罗大众共通的“性”。而认识到这种本性的共生性,将使我们能够认识并侍奉天。孟子在其经典著作中对此作出了有力的阐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一)。
因此,这是一个从个体到物种,从物种到万物之源的原则。心既是认知之始,亦是行动之本。守护内心而不让心智被盲目与冲动所蒙蔽的人,其行为自然顺应天意。与天道合一的心,汇聚万物,统摄万物:“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管,谓之心”(《淮南子·人间训》,一)。
然而,孟子所倡导的“尽其心”,也意味着清空内心…在汉语中,“一直到底”(尽)所反映的思想是祭祀动物的鲜血被倾注至盛血器皿直至最后一滴。正如老子也指出的,《道德经》第三章中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这段文字以含蓄的笔触首先表达了一种政治见解,我们稍后会来解释其含义:这句话无疑意味着要填饱百姓的肚子,但是,经文紧接着指出:“弱其志,强其骨”。同时,这段话也指向圣人本身——毕竟,根据句法,这里似乎也意指他们的心和腹——在这种情况下,文中所言是指通过呼吸而以气填满丹田,并通过反复的呼吸练习而清除内心的一切贪欲。
庄子则更强调他所说的“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四)。
用自己的呼吸去倾听,就是虚己,然后集中精神,再加以清心:所有与身体相关的生理现象都必须被完全接纳和整合,为的是在这种转变之后能完全地返本归元。由外而入的事物不会“原样”地回归自然,而是像我接收它时一样任由被转化,就像我不断被转化一样。“心斋”在于不拘泥于解释框架,即不被符号和情绪所束缚,这些符号和情绪是我理解和观察事物的媒介。心可能因接收过多而充斥,也可以选择彻底清空以重新接纳一切。唯有空灵澄澈的心,方能真正认知世界与自我,是曰:“至人之用心若镜”(《庄子·应帝王》,六)。
政治之心
《祂爱了我们》第十三条指出:“所有行为都该受‘心’的规范和指挥”。对于研读中国古代典籍的读者而言,这句话使人想起《管子·心术上》开篇之语:“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
唯有心处其道方可使身体协调运作。若心躁动,则无法发挥其正常功能,从而引起生理与心理上的疾病。在中国,心不求动,而求静,故有“心如磐石”之说。这种恒常正是仁德的体现。有句谚语说“父爱如山”,因为没有什么比山更稳固、更坚实、更可靠。对此,中医认为:心静者不易患病,因为疾病往往是由于某种情绪过激导致而成,即便这种情绪是积极的。
《管子》的这一论断也可以反向理解:如果心如同身体的君主,反之,君主也如同国家的心脏。“主者,国之心,[…]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淮南子·缪称训》,一)。
关于心的思考后来在荀子(公元前三世纪)思想中变得更加政治化,这位思想家对人性及社会制度的稳定性持悲观态度。在他看来,心是各种欲望(情)的决定者,这些欲望体现了人性(性)内部的斗争倾向。“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荀子·正名》,一)。
因此,荀子认为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善恶倾向之间作出决断,而感官则不断激发恶、并诱使人倾向于恶。心是人的主宰,是发号施令者,是我们内在生命与外显行动之间的必经通道。而从师学道的首要目的在于掌控心认知外界的方式,学会对源自外界的各种刺激作出恰当反应。学习、心境平衡乃至必要的社会管理,所有这些维度都带有人为痕迹,但人为干预恰是构建宜居世界的唯一途径,因为人性受制于欲望。
荀子关于人为干预的观念是个例外。在古代中国,心是自由之所在;但要获得自由,必须摆脱一切阻碍。对此,没有人能比孔子表达得更为精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2.4)。
对晚年的孔子而言,所追求的正是“随心所欲”。但如今,这种渴望驱使他迈向生命,迈向自我实现和众生之圆满,别无他求。再无任何致命的张力可以扰乱他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逐渐学会潜入内心最深处的人所拥有的喜悦。
- 西汉王朝存在时间为公元前202年至公元9年。经过一段时期的间隔,东汉于公元25年至220年期间统治中国。 ↑
- 参见L. Raphais, A Tripartite Self, Mind, Body, and Spirit in Earl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年。当然,中国人类学远比此处提及的区分所暗示的更为丰富。例如,还应引入“魂”与“魄”的区分。 ↑
- 关于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的精彩论述可参见D. Salin, Le Discernement des esprits selon Ignace de Loyola. Les aléas d’une transmission (XVIe-XXIe siècle), Paris – Bruxelles, Lessius, 2021, 33-53. ↑
- 《淮南子》是一部于公元前139年被献进皇宫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其成书时间稍早于此。 ↑